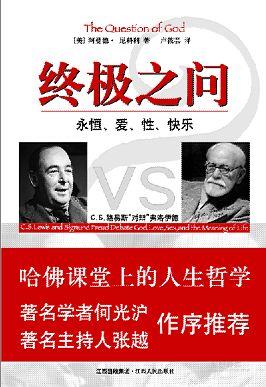生还是死,诗人和诗歌必须决断的
一、生与死,在诗人与诗歌之先
“……持罐的孩子——注视宇宙——和天空/放声歌唱——像首特别的歌/被女人/传遍世界——简单闪耀在白色中,进入延伸的田野/我从声音中开始——//做/一个上帝之子/我曾是/他唱过的一切/”
——艾基的《房子——在世界的小树林中》
生还是死?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取死?
这不仅仅是哲人、政客必须回答的,更是诗人和其笔下的诗歌必须面对和表达的!这个问题再不明确,诗歌必如末世混乱一样乏起无数的虚假的恶之花,即便有旋涡中的挣扎、点滴的希望也被无情地消耗泯灭,而陷入彻底的灭亡中。啊,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了!且不论诗歌,单看看现在好些诗人的生活和灵魂状况吧……
在脱缰的马车狂奔的道上,谁才可以真正地将您救赎?永恒的审判前,诗人啊,谁可以抬起您的头颅?除了那在永生前低下头,谦卑地渴求的!或说我不是在歌唱生命、叹息生命吗?诗人作为人类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就是为此而生的呀,我怎么就与永生无份,反受审判了?
这首先就要清楚“我”是谁?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向生,什么是向死?诗人们,必须对这些问题正本清源地做出回答了!否则诗歌的堕落与加倍的边缘化势在必然——不是诗歌被大众和社会撇弃,而是诗人本身就把自己抛弃了,在光明的生的道路上。
赦舍尔说不能问人是什么,而应问人是谁,即问人是谁的形象和样式。诗人们,真正地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何灵魂里应当比常人更兴盛的您仍是诸如此类的声音不绝如缕:人是经济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偶然的存在;人是命运的无奈……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写诗,我只知道我是诗人,诗歌就是我的命运,除了诗歌我别无所有……
诗人啊,如果您放下“我”——知道我不是大写的“我”,我不是荣耀的诗人,写诗也是不我的命运;您就可能清楚地看见“我”只是和其他万物相同的一个被造,但“我”是拥有神灵的形象和样式的被造,而且“我”不过是有幸蒙召来作为了赞美那创造“我”的一分子——这时全新的智慧的门打开,对于命中的生死祸福便自然有了透彻:就像鱼只有生活在水中,鸟只有在天上飞,树只有扎根在土壤里才能自由地生息一样,“我”只有和造我的赐我生命给我力量的那一位神融合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才能真正地发出诗歌的妙音!并且一定是先获得生命,再有生命的诗歌,就如先有了那位全能的生命的上主,才有“我”的幸运和在诗歌里的幸福。
真理就这么简单:和造“我”的神在一起为生,和神分开为死,我衰微、神兴旺为向死而生,相反神衰微、我兴旺为向生而取死。常说“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尤其中国诗人欣赏相濡以沫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回到水中、回到生命的原理中吧。人在生命原理中才能成长与安息,人也只有在生命原理中才能完全迸发出创造的活力。这对于诗人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神所定的生死存活的根本,而诗人们是最敏感,最接近神又最容易远离神的一群!
二、为什么最接近的易成最远离的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叶芝的《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
“得真理者得自由”,什么是真理?希伯来原文说得清楚:事物的本质,生命的本质。这万有的本质是什么?《圣经·旧约》中“神”是伊罗勒、伊罗、伊东乃,这在古希伯来文的原意泛指“能”、“能量”,或“最高”、“最上”、“大能”,是复数的总称,和《道德经》所说的“上善”、“太上”类似。这最高的创造主常用一个喻词表达: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意思在中国古时表述为道生一,道为万有的源起。但是老子认为这道非常道,不可道。而由神默示给人的圣经中分明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救恩和主耶稣的救赎使命自然译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如此简单明了的真理为什么反被隔绝,有眼却不能见、有耳不能闻呢?圣经用伊甸园的故事明白生动地显明人是怎样陷到罪中,与神分开的。对于自以为满有智慧的人来说,这个故事近于童话,哄三岁小孩的,毫无逻辑与可信性。真是“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其实真理从来都是朴素的!撒但的英文意思是:挑拨离间者。那撒但通过蛇来引诱亚当、夏娃就是离间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也随之破裂,痛苦由此而生。正如刘光耀先生其《诗学与时间》中说:“诗不发生在人与世界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与上帝之间。归根结底,诗乃罪人所吟……抒情诗以及全部所谓美的艺术发生就是以人和神的分裂为前提的。”
为什么亚当夏娃经不住诱惑而中了撒但的计?首先是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让人在经历的一切事上去真正地认识神、体会神、享受与神的同在。是就此妄自尊大而陷进痛苦灭亡的深渊还是像约伯一样确信“你试炼了我,我必如精金。”而走在真生命的路上?另一方面是人的自我膨胀给撒但做工留了余地:“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想如神一样多好,我想我肉体肚腹和眼目的情欲都可大得满足……就这样,当“我”的需要在先、神的信实在后的时候,一条充满“美丽”诱惑的迷离路也展开了。在这条路上,“我”还能回去吗?当然能,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生命……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人,是人离弃了神而自取灭亡。即便如此,神仍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来显明他永不见弃的爱。只要转向神,向死而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
但为什么这个转身如此困难?仔细读读从人类初始的诗歌到当代的诗歌,诗歌的堕落历史几乎没有逆转过:在情感中自娱自乐,再到在语言的游戏间转,在自诩的各种流派里喧闹……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了从全民皆写诗到全民不读诗。有人归结为高科技时代人们娱乐休闲的方式越来越多,诗歌的空间越来越小,真是灵眼昏暗,不见其本,谬之远也!
德国的萨弗兰斯基的《恶或者自由的戏剧》深刻揭示了为什么撒旦容易在诗歌与艺术里做工,简而言之:神赐予了诗人很多的厚爱,把赞美天使的荣耀加给他们,让他们对生命与美的领悟更敏感、更丰沛,这赐予的本意是神要他们更好地发出神的声音,传达神应许的消息,由此带领迷惘痛苦的人恢复和神的关系,开启和发现无处不在的美!可诗人们总以为这赐予是自己的才华而自我陶醉、自我炫耀,并以此为局圉限制,到死也以为自己比天大。故即便灵光闪现,不乏佳作,离地狱也不远了。魔鬼也是大有智慧和能力的,但它绝对是把人带向死,而不领向生,太多自杀或精神失常的诗人便是明证,以致世人在某种程度上把诗人和疯子、精神不健全者、生活低能者、经济潦倒者划等号。
对此,刘光耀先生一语中的:“人自命的神性愈多,他身上的神性愈少,从而离神性愈远……抒情诗既可以充当人与神的使者,也可以扮演以人代神的恶魔,既可以作为人的“在上性”的侍奉者,也可以成为那在上性的“侍奉者”。”当人成为人的“在上性”的侍奉者,不管他自认为自己多神,神性愈少,从而离神性愈远……抒情诗既可以充当人与神的使者,也可以扮演以人代神的恶魔,既可以作为人的“在上性”的侍奉者,也可以成为那在上性的“侍奉者”。”当人成为人的“在上性”的侍奉者,不管他自认为自己多神,神圣已经远离,并使之成为笑柄;当人成为那在上性的“侍奉者”,不管他认为自己多么无能不配,神将他高高举起。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拥有绝对的主权!若明白神永恒的慈爱的心,在等待浪子回头,等待诗人由衷地献上赞美,献上对离罪去死的生的歌咏,那才会必得生命的荣耀的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