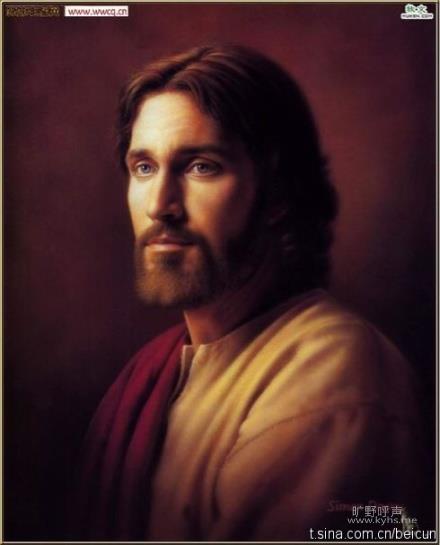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诗人与诗歌
三、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诗人与诗歌
“几乎没有什么亲密温暖的事物/仿佛我们从未作过儿童/我们坐在屋里,在月光中/仿佛从未年轻过,这是真的……”
——华莱士·史蒂文斯的《生命和心灵的碎片》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直是在个性人格中反映普遍人格,即有人人皆可尧舜,人人都可成佛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基础是性善论。道家虽没明确提倡性善论,但内在倾向还是主张性善的,以返璞归真为理想。相信性善,那么自我的修养和努力就至关重要,以通过生命内求式的道德塑造来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没能为解决人性恶问题留下相应的处理通道。对此黄仁宇在其历史著作中一再有阐述。
于是中国的知识对象与理想生活很早就集中到人文整体的共同目标上。儒家精神是对成圣的向往和崇拜,有了圣人就不需要神,中国传统的至高理想是人人做圣人。道家的理想是做真人,其实仍在儒家的立场补缺救弊。这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表面的早熟——在社会制度内精光凝聚,却少有生命横溢奋发之真趣——任何一种知识和事业,都是达到整个人文理想的一个工具和途径,而不是在神的启示带领下因信得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都在于使人人成为圣人,也就是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的最高
境界。从这个角度,梁漱溟先生指出这是中国没有出现大统的宗教的主要原因,文化就是中国的宗教,不需要别的了。近年来热起来的国学复兴、新儒家等基本上还是在这条思路上走,但这也吸引了不少诗人迷在易经、气功、修道、弄禅里,还自以为得了真道,又生出另一种骄傲来。
这种生命的认知方式从理论上的确非常美丽迷人,也没有什么不
妥帖可一眼望见破洞之处,真是一种很好的人文理想。但为什么这样的理想不能很好地付诸实践呢?因为对于人的被造性确认太少,对人是怎样的存在模糊的多,在自求的过程中人性容易进入以为生命的某种规范就是道德的误区,以为仅仅遵守道德、律法就正确而完美,且可一劳永逸。其实这背离了唯有神的爱让律法完全的本意,结果离生命越来越远。就如摩西十诫守得再好却忘了真道,耶稣基督来了也不能得着救恩。
若说春秋战国时期还显示出人的活力,从秦大一统后,中国文化逐渐丧失生命力。总夸耀中国唐朝如何风光,由此来证明中国文化如何了得,其实人自以为了得的时候,也是给魔鬼的空出地步最多的时候。所以在宋以后的理学进一步滑落,根本就在于用生命的光派生出的道德偷换了生命的本体之光。应该说中国三四千年前就提倡人道,注重天人合一,这是神的恩典下的对巫术、图腾的超越,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显得聪颖早慧,但把生命的光简单纳入自我推论的天理体系,则把中国人的生命活力阉割了,故鲁迅对此恨得牙痒,说书里只有两个字:吃人。
如此注重自求而绝于神明的思维方式让中国文化在对真理的追寻过程中陷入分裂,受尽国家与个人命运颠沛流离之苦,希望一再破灭之痛!几乎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出则儒,行则法,
退则佛,隐则道……表面百花齐放实则已经败坏——人与人的儒家伦理文化,人与自然的道家自然文化,虚与实的佛家轮回文化等“思想鳞片”难以观照出生命之光的全备真理。在此文化精神下的诗歌艺术只能在感情的内泄中的完善自我,从而让灵魂趋向净化——从屈原到苏东坡,从苏东坡到纳兰性德,中国文人一直在追求人格与审美的完善。这境界让中国诗歌美则美矣,了犹未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关注地上的事情,钟情于“我”的感觉和抒发,以至诗歌的时空想象力和人文原创力被不断削弱,其间跃动的生命之光越来越黯淡。
在此文化精神下中国的审美思维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定罪定到死,定自己的定别人的……屈原、司马迁、鲁迅等愤怒派代表;一是出世逃离不以罪为罪,人与我何涉、我自潇洒……庄子、李白、周作人等逍遥派代表,一路走来在两种趋向中力求平衡而又难以协调的犬儒派则数不胜数。这样一直摇晃到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式宗教几乎完全失去了拯救自身的力量,清z /-府对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极度打压,传统中固有弊端和欠缺日趋显露,三教并流的分裂性又产生不了更有强有力的文化凝聚,其调和的多,创造的少。大兵压境之下,国家民族何去何从,是生还是死,已经刻不容缓!该怎么办?该走什么路?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当时不管什么样形式的拿来,过去的妄自尊大又都或多或少地变得妄自菲薄。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诗可谓先天不足,既没有弄清外来的优劣,也没有继承自身的精华,更看不清当西方世界离开神以及神圣启示的同时,其诗歌和艺术也逐渐变得荒谬而欠缺生命的理性。但不论怎样先天不足的新诗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在神的保守中,从五四至今,中国的新诗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不少作品丝毫不逊色于世界一流。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各帮派”中心优势的倨傲与边缘对优势中心的误解或误读、互不买账、小圈子意识、自我膨胀以及功利、操作、行内权利话语争夺等;诗人似乎天性中的偏执极端,实验书写中的我行我素,也加速了矛盾分歧,制造了不少的肥皂剧。更重要的是对于生死的取向和真理的不明确,当今的新诗还显不出生命整全的勃发。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