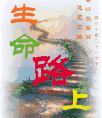在苦难的炉中——你拣选我(2)
三、启行火车驶向何方?
1988年夏,我坐火车东行再转南方。博格达峰顶的冰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火车穿过干旱的戈壁滩,驶过黄土高原,进入四川盆地。
出生在新疆的我,第一次进入内地。
入夜,听着火车运行的声音,看着乘客东倒西歪地睡了,我惊恐不安。火车头离我坐的车箱有多远?窗外黑漆漆的,仿佛列车无人驾驶。我恐惧,我的生命也如这列车无人驾驶。我流泪了。
它会开到何处?它要开到何处?它能开到何处?
仿佛前方有一道巨大的裂谷,火车就要冲进去了。那大裂谷空寂无声、深不可测。
我随身携带着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还有一本《圣经》。《圣经》是妹妹留给我的,我没有打开看,我只看那本由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我的旅行的时间很长,
旅途也很长。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
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
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要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
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
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
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我心中的茫然都在这首诗里。未揭晓的日子也预言在这首诗里。我的旅行开始了,可我看到的却是窗外的黑暗。火车仿佛无人驾驶。我的前景也不可知。这样的恐惧一直持续到天亮。
火车进入广西境内,石林和甘蔗林暂时占满眼目;暂时挤出了我的恐惧和虚空,让我稍稍平静下来。
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又乘船过琼洲海峡,上岛。
四、椰风灼焰
上岛的第一印象就是白天的太阳光焰灼人,夜间的蚊子成群叮人。
口袋里的路费用完了。我看到拥挤在海口的大学生,多得惊人。椰树下,东湖边,只要有广告栏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我在街头饺子摊上帮忙,可以挣口饭吃。“四海之内皆弟兄”,一起干活,一起等安排工作的机会。
街头,花枝摇曳,海南岛的女人戴着斗笠,削菠萝来卖。小孩卖甘蔗。这样也能活命,我就不该怕了。
在我们租的旧楼,往来着许多大学生。也有没考上大学的用卖血钱作路费来闯海口的高中生。那时,逃离大陆,逃离原有体制困境的人有十万,解放军报的记者雷铎报道了这一情形,《十万人才下海南》。其实,当时海南特区,街上连盏路灯都没有,大排挡里的照明用电,是用小型发电机发送的。海口真是一穷二白。无企业,无工厂,无接收单位。满大街海南人,都穿拖鞋。穿皮鞋的都是“下海”的大陆人。砸了,这哪是立身之地?
渐渐地,开始有公司立足了,也有短期就业的机会了。也有人开始发迹了。也有女大学生作小蜜了。我一再挫气,我的政教专业非常不好找工作。我面对成功的下海人士,真是困惑。
白天,我站在街头卖饺子;晚上,钻在蚊帐里写长诗《哪来哪去》。我是谁?我能做什么?从哪来?到哪去?
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何处,我的帮助在何处。我也无法回原单位了,我前脚离开,他们就给我除了名,我从自治区科干局办的停薪留职批文,我的工作单位不承认。
五、白玉兰
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来到海口的一所老教堂里,一位老人扫着院里的树叶。我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泪流不止。
我不懂这里的规矩,不知道什么敬拜。孤独占满了我的心。
教堂门前,有一棵老老的玉兰树。树杆苍劲,满身裂纹,裂纹里生满了青苔。枝上的玉兰花开得洁白无瑕。我的心里都是污痕,灰暗。
我徘徊彷徨挣扎,我该怎么办?我到海边,我望着大海,望着天,心中求告,帮帮我。我在沙滩上写诗,写一行,海浪扑来抹掉一行;写一行,海浪扑来抹掉一行。海口,不是写诗的地方。我始终没有打开那本《圣经》,我不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