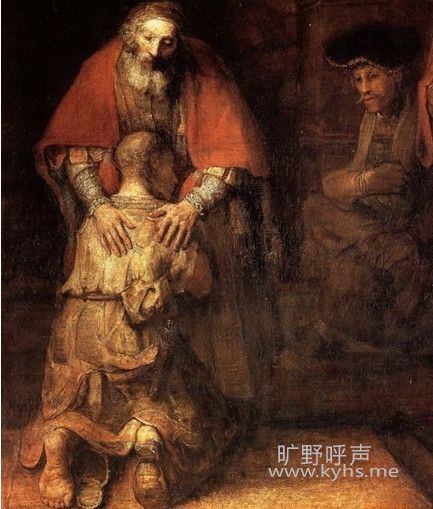韩婆婆的故事(八):格格不入
我正式被任命到烟台学校之后,事情就进行得很快。这学校暂时使用已经很拥挤的上海总部。星期六上午开校务会议,在会中我知道了自己的任务——要教校内所有的自然科学,包括初中高中。年纪最小的班级为九或十岁,相当于美国的小学五年级。全校总共有七班,这工作听起来已够令我担心的了。但我最怕的不是工作的负荷,乃是必须教小孩子。我喜欢教大学生,我在大学教书胜任愉快。但我毕生却从未教过一个小孩子!“好吧,我就姑且一试吧!”我想。
我立刻发现在烟台当老师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教课——我在校务会议里就撞上了。我是唯一的美国人,其他教员都是英国人,而烟台完全是照英国制度进行的。举例而言,他们一直谈到form的事,我却完全不懂,我以为form要不是假模特儿,就是申请工作或学校所填写的表格!他们也说到甜的食橱和火把,我真是搞糊涂了。会后我的疑惑得到了一些解答——原来form就是一班学生,甜的食橱是放孩子糖果的地方。“火把”原来是手电筒。如此,我在烟台受的教育开始了!
时间过得太快,星期一早上要开学,而我惦念着整理教材。我去找校长求助。
“我到哪里找教科书?”我问他,“我真的需要为星期一的课做准备,我必须先看看那些书。”
他的回答叫我大大发愁 :“我怕我们没有教科书了。”他说,“我们所期待来教这课的老师,应该是会带教科书来,但很抱歉,因为那老师没有来,也没有教科书了。”
我的心往下沉,简直要哭了。我要教七个不同年级的自然科学,而居然没有教科书,这怎么可能?我几乎没有声音再问下一个问题。“实验室的设备怎么样?”
“没有什么设备,也没有实验室,我们什么都没有!”他有点难过的回答,“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在战时被日本破坏了。书都与学校校舍一同被烧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能说什么呢!而谈的结果只有无助和绝望。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心情到了低谷。回到房间,我孤注一掷的向主求救。“我现在怎么办?主,我怎么可能这样教这些不同年龄的班级自然科学,没有任何设备器材,而更糟的是,这学校的制度我完全陌生!”我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一道不可能跨越的障碍前,因为孩子们在课堂上不是需要娱乐而已;他们还要准备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入学考呢!我继续向主哭诉:“祢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我来中国不是为这些!”我一直抱怨。正如你所猜想的,我几乎要回到华福兰那儿告诉他:“抱歉得很,我不能作了。”但我里面似乎感觉那也不对。好像我的心对我说:“挑战来了——尝试看看吧!”
我平静下来后,开始再重新估量整个情况。我唯一拥有的科学设备就是显微镜。那是我自己做研究的显微镜,当时决定带来中国而不在家乡卖掉。现在我真感谢主让我带了它来!但我怎样安排像化学和物理这一类的教材呢?看来简直不可能。
在上海的中国内地会总部的这些日子非常拥挤。场地虽然大,还是不够大。学校和学生的宿舍都在里面;办公室也在这里面,再加上战后宣教士们回到工场路经上海也暂住此。在这里大家息息相关,互受影响。这种时候正是容易滋生误会的时候,我不了解我的同工们,后来我也发现,他们又何尝了解我。这种情况的考验很大,而我又要面对这样沉重的教学使命,真不知道怎么可能在这三个月度过这双重的艰难。三个月!我简直一天天在数!但主在这段日子对我似乎有特别的话语:“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在充满挫折感、情绪低潮的时候,至少可以信赖主的全知,以及祂的作为。
现在我常常奇怪,最初的那几个礼拜,我到底教了些什么,怎么样教的。我甚至不知道怎样管教学生。而课堂上并不是我最花心血的地方。我们对孩子们还有课外的责任——例如休息时间要陪他们,或帮他们擦背和打小蝴蝶结!
我对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没什么概念,不知要如何帮助这些孩子们准备,但是很奇妙,恰巧在我们总部的隔壁,就有一个很好的自然科学图书馆。那儿可以找到旧的考古题,从这些考题可以做出一个讲义的摘要。所以我开始觉得教得有一点头绪。但是大部分的课,我更像一位魔术师从袖管里变出魔术来。我真的可以把魔术家的兔子用来做实验室的标本!虽然我们没有兔子,但却有些滑稽的事。例如,青蛙的插曲。
那是从我的挫折感开始的,因我发现上海实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实际的做像样的实验。总部完全没有可供做生物和植物学实验的地方。生理学方面我较占优势,因为那是我所学的专长,而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讨论自己的身体。
有一天,我答应班上要让他们观察青蛙脚上小血管的循环。我很有把握不难找到青蛙。所以当我在休闲时间照顾他们时,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抓一些青蛙,为明天的课做准备。”我不必再重复一遍,孩子们已经立刻跑出去热心的到处找青蛙了。
平常,总会有青蛙在总部的草场上,但你想那天下午有人找到青蛙吗?绝对不!连一只青蛙的哇哇叫声都没有。似乎有人警告过它们呢!多失望啊!我知道第二天的计划粉碎了。
忽然我听见从院墙的另一边有一群声音。是青蛙!它们正伸出头在哇哇叫,好像在愚弄我。我推断它们在隔壁寺庙的花园里。现在需要行动!在休闲活动之后的一点点自由时间,当孩子们要整理收拾时,我很快的翻开字典看看怎样用中文向人要一只青蛙。然后,没有告诉人我去哪里,只请了另外的老师看管我班上的孩子一会儿,因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她毫无问题的答应了。然后我很快的出了前门。绕着角落走去,尽量不引人注意的一遍遍重复念着青蛙的片语。当我到达寺庙门前时,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走进去。和尚和道士们,都穿着橘黄色的袍子,很奇怪的看着我,问我来做什么。窘得要命,我说出了要一只青蛙的请求。自然的他们问我要一只青蛙作什么,我尽力的向他们解释。多强烈的反应呀!他们吓坏了,我知道并不只是因为我的破中文。我对佛教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尚们严肃的告诉我,那些青蛙——那些微小、哇哇叫,可以变成很好的科学示范的青蛙——是神圣的,前世的人,再化身为青蛙。因此科学和宗教就进入一种僵局。我确定要不到一只青蛙作科学实验了!我不记得他们领我参观过哪些地方,只记得自己尽快的从庙中跑出去。
我回到学校,自我嘲笑一番,但却不敢把自己跑出去的细节分享出来,免得也许会被骂一顿。因为我的无知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我现在还是没有青蛙。我已经准备好了其他的课,但没有东西可以准备生理学。那天晚上我祷告时,只简单地说:“主啊,我好疲倦。你必须为我预备一些东西——我实在不知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轮到我要陪孩子们,很晚才吃早餐。当我走进餐厅,一位坐在大餐厅最远一角的同工叫我的名字:“宝琏!宝琏!好消息!你能不能用老鼠?”
我忘形的大声回答:“你有老鼠吗?啊,神听了我的祷告!”结果哄堂大笑,在两百个食客对疯狂科学家的笑声里,我跑出去拿老鼠。因为头被打伤了,所以那老鼠昏过去了。我接过手来,破坏大脑,使它的身体功能持续。这是对动物非常仁道的方法。
幸好当天的生理学是第一堂,而老鼠虽已昏迷,心跳还很正常,我解剖开那只老鼠,指出循环系统给他们看。每一个人都很兴奋,很热心的看,又不断讨论着。有一些孩子告诉他们的家长:“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现在我们真正要面对问题了。”很不幸的,有些家长不喜欢这种教课的方式,他们来告诉我,他们不赞成他们的孩子看这种东西!我十分痛苦,因为我的辛苦毫无意义。这样的谴责好像一棒打断了骆驼的脊背。我实在觉得很受挫折,就跑去找华福兰。
“华先生,你要我在这学校教书,”我开始说,“我必须知道一件事,到底我在这里教自然科学是照我自己认为该教的,还是必须听所有家长的话?”
“好,请详细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很有耐心地说。我就告诉他,是什么事情使我困扰。他很表同情的听完以后,回答说:“好了,宝琏,你可以照你认为该做的做。我相信那不会对学生有害的。”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心里很得意,重新恢复了信心。我有了从最高权威来的指示,自此以后我不再注意那些埋怨了。事实上,后来有些家长因他们孩子真正有所学,来向我表达谢意。因此,我也顺利地跳越了另一个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