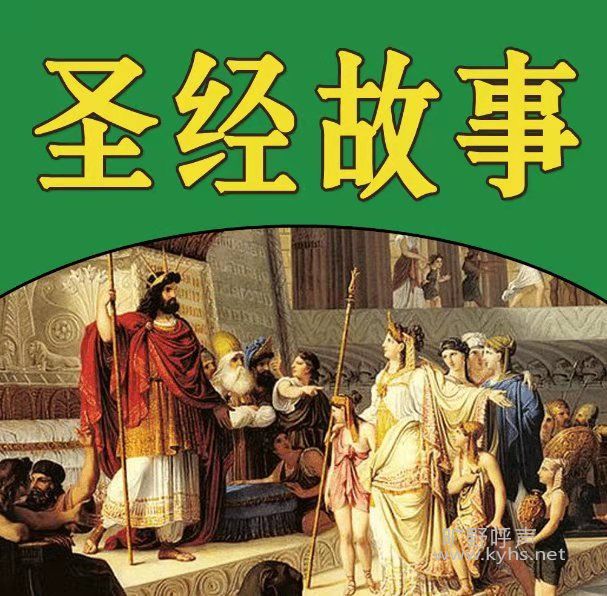蜘蛛的母亲
蜘蛛的母亲
大漠
乳白色的阳台上,摆放的几盆鲜花,被斜进的阳光刺激得似乎抖颤了几下。我的眼睛盯住那朵好看的红月季,觉得她的样子,很像一个娇羞的小姑娘,在与我目光相撞的一瞬,好象她垂下脑袋,歪起红晕的脸蛋,斜着笑咪咪眼睛,在偷偷地觑着我。我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可是,就在这一刻,空中响起了一阵嗡嗡之音,一只圆肚花纹的蜜蜂从上面突然地降落到月季花朵上。也就是在这时,我才发现花盆与花盆间缠绕了一片蜘蛛网。悬在网上的母蜘蛛猛地举目而望。阳台的空气蓦然显得紧张而寂静。蜜蜂的翅膀呼扇着,于花朵间打着旋儿,缭绕着,一飞一落的。
悬在网上的母蜘蛛,伸开了她的六条腿,拱身而起,蹑手蹑脚地从花盆底处爬上来。沾了花粉的蜜蜂,静落在花蕊中,拱着脑袋把嘴探入花蜜里。一下下,一点点,一秒秒地品尝着蜜的丰盛和美妙。灿烂红艳的月季花瓣上,陶醉在幸福甜润的蜜蜂背后,母蜘蛛慢慢地露出身子,孑然一跃,只在刹那间猛地跳到了蜜蜂的头上。蜜蜂一机灵,慌忙振翼而逃,并用他锋利的毒针朝母蜘蛛刺去。蜜蜂身上的花粉因为彼此的扑打而纷纷溅落,阳光下像似点点的飞星,舞蹈着散落在花盆左右。谁知,母蜘蛛任凭蜜蜂的狠毒和挣扎,始终咬住蜜蜂不松口,有骨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气势。
终于,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不一会儿,蜜蜂的翅膀失去了灵敏,脚也不听使唤了。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朝空中刺了几下,再无反攻之力,只有薄薄的依然光亮的翅膀还在微微地颤动着。他的翅膀和脚上沾满了喷了香气的花粉。母蜘蛛的身子一动不动,表现着胜利者的安静,英雄似的伟岸,一点一点地吸吮着蜜蜂身上的鲜血。
可爱的阳光,把月季花照得泛起一片灿然,在白昼的寂静中,她和我一样旁观了这么一场掠夺和殊死的争斗。表面美丽的母蜘蛛,黑玻璃一般的眼睛,灰缎子似的肚子,却长着坚硬的节足,它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举动,俨然英雄,又好似邪恶的魔鬼。这种残酷的悲剧,于岁月的悠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可是,只顾打扮自己的月季花,每天依然在灼热的阳光中过着花姿招展的日子。过了不久,母蜘蛛在白天里,钻到了月季的叶片和花朵之间的空隙里,爬上一个枝条。枝条上的花苞,让酷热的空气及强烈的阳光烤得似要枯萎,花瓣呆在一厢,忍受着酷热,微微地抽搐着,颤颤地喷放着微小的香味儿。蜘蛛在花苞和枝条之间往还地爬着。这时洁白的,流淌了光泽的无数蛛丝,渐渐地缠向有些枯萎的花蕾,缠向愣着神的枝条。不一会儿功夫,这里出现了一个好象绢丝结成的圆锥体的蛛囊,白得耀眼,反射着盛夏的阳光。母蜘蛛做完了巢,就在这美丽的巢里,安静地产下无数的蜘蛛卵。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自己坐在上面,然后撑起一张拱圆形幕布似的丝网,只留一个小小窗口,灰色的母蜘蛛被遮盖起来。然而,,母蜘蛛的身体显得愈加瘦弱,或许是产后才叫她这样的。她躺在阳台的一角,呆傻似地安卧着,以往的一切英雄壮举,似乎被她早已经淡忘了,什么月季花、太阳、蜜蜂的,她显然忘记了这一切。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母蜘蛛的囊巢里,无数蜘蛛卵巢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对这件事最先注意到的是静卧在阳台一角的母蜘蛛,她已经是一副萎缩而苍老的样子。她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地蠢动着的新生命。她移动着,一只脚一只脚地移动,缓慢而无力。她咬开了母与子相隔的囊巢顶端,于是,那无数的小蜘蛛不断地从这爬出来,丝垫变成了百十个微粒子蠕动着。
小蜘蛛立刻钻过窗子,一拥而上,一部分朝月季花的枝条上爬去。它们拥挤着聚在叶片上。一部分爬进喷了蜜香的月季花瓣里。另有一部分纵横交错于阳光郎照下的月季花与枝条之间,开始睁开眼睛,陌生地端详着周围的一切。
然而,瘦得如同影子似地母蜘蛛,寂寞地蹲在卵巢边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睁一下。过了好久,脚也不伸一伸,逐渐地僵硬在那,依傍她的只有枯萎了的月季花苞的淡淡地馨香。她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纱幕般地阳台间,完成了做母亲的天职。
【作者简介】 大漠,2009年8月28日在沈阳东关教会受洗归主。2012年开始在《雅博网》网站做文字侍奉至今。先后在《信仰之旅》、《文化中国》及网站发表信仰文章近200篇。现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