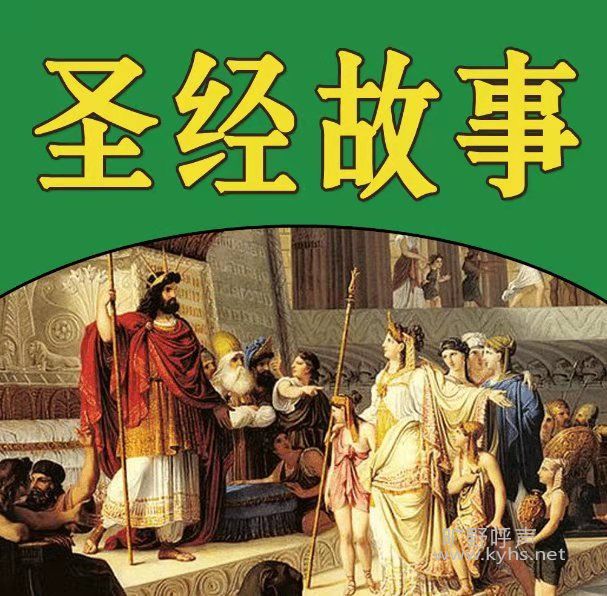夏 日 花 溪 (昔日作品)
那年夏天,与同事留连于花溪的真山水之间。
夏至后的第七天,已是盛夏的花溪,依然凉气逼人,是个好睡的时辰。但凡在花溪的居所,我总是思绪万千,见景情生而缕缕真切。
门儿轻掩,独自南行不足百步,已是暮霭时分。又弯到了去年的荷塘时,全身已沐浴在水雾之中。不经意的回首间,猛见到几树荷花,在紫雾中亭亭玉立,惊喜非常。现代的都市,绝少见到荷花了。偶然见到的池塘,仅比木盆大几倍,至多也是几朵睡莲,恹恹的,小家碧玉罢了。而荷花,硕大如伞的叶,高挑带刺的茎,肥壮的莲蓬,清纯如佛面。
依稀见得那初夏时欢快的花瓣,已开得有些倦意,恹恹的要垂下眼,瞅着将睡去的睡莲。荷叶已在残破,墨绿里无奈地透出焦黄。莲蓬勾着腰,孕着肥实的莲子,在晚风中晃动,浅浅地吟着摇篮曲。蛙鼓小心翼翼,高一声,低一句的应和着。
花卉草木一岁的枯荣,偏让我赶了个晚,心里总有点悻悻然。清纯的春,浓情的夏,匆匆而来,怅怅而去,秋日又将来临,之后又是一冬长长的企盼,让人留下深深的叹息......。
夏至之前,花溪发了大水,且不说小溪们欢腾跳跃,横溢着热情,就连山坡、小道,也象熟透了的水蜜桃,胀得满满的,都是汁儿,不用挤,吹口气,都会流淌出汁液来。长满青苔的岩石,也汗淋淋,湿漉漉,情切切。溪水不再碧绿,不再温柔,裹挟着山里浑浊的色,野性十足的从四乡涌出,把花溪鼓荡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成熟的、乳香般的腥味,撩拨着人模糊的、莫名的欲念。
离了荷塘,溯溪而上,那水声越加欢腾,象一泼乡野赤足的顽童小丫,从坝上、田坎、跳蹬、沟边、涵洞,从一切可以向下的地方,跑着、跳着、跃着、蹬着、蹿着、挤着、钻着,发出放肆的、喧腾的、夸张的、无序的声响。象锣、鼓、钹,象丝、竹、弦......
也是在这溪边,1944年5月8日,青年巴金和萧珊在这里的“花溪小憩”结婚,巴金老人这样写到:“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溪水知道吗?它们曾经伴过一对青年的蜜夜,那青年也为它们回馈了一篇《憩园》。
花溪如画,不象西洋的油画,色彩斑斓,而是水墨画,泼墨留白。那白,就是静,就是空,就是遐想,就是无限。心静,那涌出的或是磅礴的交响曲,或是沁入心脾的江南丝竹。内空,“楼空得月多”,那“空”处可以挥洒任意的色彩。而那无限的遐想,则随人随缘了......。我想,这就是真山真水的花溪的魅力了。
花溪少几分雅趣,却充满十分的野趣。
三月,菜花香十里,八月,十里稻花香。夏日里,溪水中,浮现出老牛的头和背,和着哞哞声的,是牛背上的八哥。柳树荫下,布依老农懒懒地斜靠着,任意地享受天地的灵气,随意地打发着时光。花溪游人们漫步的路,都是四乡山寨农人们的生计之路。布依女们,踏着晨露,担着她们的菜啊花啊,鸡啊蛋啊,飘飘而去......;暮蔼,撩着炊烟,揣着她们的衣啊布啊,脂啊粉啊,呢喃而归......。
夏已老而秋将至,人心又生出许多期盼来。期盼花溪秋收的丰饶,期盼黄金铺就的大道;期盼悄悄壮实的莲藕,期盼秋水清清、伊人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