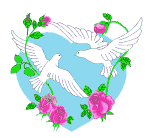不能做的爱
就在猪肉价格上涨期间,千小峰喜欢上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有点喜欢他。手也牵了,吻也吻了,离上床就差一步了,却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对女孩子来说问题不大,对小峰来说,问题不小,因为他是个基督徒。
本以为信主后啥问题都没了,没想到却产生许多新问题,比如牵扯到性,很多基督徒认为性是为婚姻预备的,婚前不可上床,不爱哪能做?!这让小峰感到有点苦。谈恋爱,对男孩来说,就是跟异性身体减少距离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每天减一点儿,否则回到宿舍床上,怎么回味也觉得今个儿的爱恋得不尽兴,任务没完成。不做哪能爱?!爱得到做的地步,才算战果辉煌了一把,免得舍友们谈起这方面经验来眉飞色舞,唯独他还是处男一个。当然,有时小峰自己也有点犯糊涂:到底他是在爱对方呢还是在利用对方来结束自个儿尴尬的处男生涯?
算来算去,结束这一生涯之障碍有四:第一是对方,每次进攻,女孩也会抵挡那么一阵。像是半推,更像是半就,每每弄得小峰更是兴起,下身鼓胀胀的,最后也总还是依了他,在蜘蛛网后边气喘吁吁吻下来,小峰很满足,女孩似乎也对自己颇有姿色到能使男孩猴急很满足,真有点像渡边淳一女主人公那样欣赏他那不能自制的淫荡的味道,虽然有时舌头上还夹杂着吃完青椒土豆丝后葱花的味道。第二是避孕,到底是男方用套,还是让对方吃药?小峰有点拿不准。爱情得无备而来才像是爱情,但这总得事先准备,万一怀上怎么办,基督教不准堕胎,更麻烦。小峰在超市买面包的时候,干脆顺带买了一盒,做到有备无患。第三是地方。那一次,和女孩肩并肩在校门口小店里逛,一出来就碰见一个中年妇女,拿着个小牌,诡秘地对他俩晃着说:“钟点房出租,有热水、电视、空调,二十块一小时。”两人的脸一下都红了。脸红归红,千小峰对此却想入非非了好久,这意味着第三个障碍能顺利解决。最后一个障碍就是他的信仰,说到底这是唯一障碍。
他专门查考《圣经》,发现《旧约》对以色列人有这方面的规定,似乎早过时了。“十诫”第七诫“不可奸淫”过于笼统了点,再说“十诫”是不是也过时了,毕竟这已不是律法时代,现在是恩典时代嘛。《新约》中,有些经文隐约触及到这问题,《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可未婚同居算“苟合行淫”吗?这里的“床”到底是婚后的床还是婚前的床?
小峰去找团契带领人。带领人非但没鼓励他“大胆往前走”,反根据《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他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根本就不可以开始谈恋爱。啊?这是指着谈恋爱说的吗?小峰不大服气。“当然包括恋爱。”那位带领人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同理心!律法主义!”小峰心里嘀咕。对带领人一肚子意见。
“离开这个团契,过自由自在的信仰生活。”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响起。“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另一个声音说。就这么斗争来斗争去好久。
这让小峰很郁闷。他不确定带领人的解释一定对,但也不敢说他就错了,何况他内心深处也隐约觉得他真正爱的似乎不是女孩这个人,而是她性感的身体。每次吻完了,满足过后,总有那么一丝丝疑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女孩还老不愿回去,也让小峰有点烦。
那就先带女孩信主再说。于是,小峰每周都带女孩参加小组查经。他借助《圣经》向她的灵魂布道。查经结束后,她借助身体向他的肉体布道。灵魂总是打不过肉体,他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到了初夏,女孩喜欢穿短裙和高跟鞋,走起来很暴露。每次查经,女孩似乎不过换个场合跟他约会。
随着距离接近,约会甜蜜期早就过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大有因误解而接近因了解而分手的趋势。
有一次,女孩的父母来了,她不能参加查经,又不愿带他去见她父母,他就一个人去了。查经还没结束,他就迫不及待约她见面。她过了好久才到老地方来,一见面还没怎么吻就说父母叫她出国,希望她以后找个城里出身的男孩子。小峰最反感女孩看不起他出身农村,家里穷,一听就来火,跟她大吵一顿。女孩也特别厌烦他自卑而又极度自尊,敏感到可笑地步,一赌气扭头走了,他也没像平常一样拉住她。
女孩走不多远,刚到化学楼高楼边,上边猛不丁跳下一个大学生,自杀的,十一楼跳下来,撞在自行车棚竖起的铁柱上,脑袋撞裂,溅了女孩一脸白的脑浆和红的血。“砰”的一声,她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黑暗中用手一摸,就着边上的光线一看,当场尖叫起来……
办理休学手续后,女孩的父母带她到了很多医院,时好时坏,没有根治的办法。小峰天天为她祷告,倒是很迫切,也请团契为她祷告。他隐约觉得这是上帝的管教,但又有点埋怨这管教有点太严厉了,使他无法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后来,团契带领人告诉他烟台有一家基督徒办的精神类疾病康复学校,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还有家长陪着,边祷告边吃药,双管齐下,很多人好了。小峰就联系上,让她父母带她去那里试试。她父母很反感,要不是他约她,不是因为两个人吵架,女儿怎会碰到这事?就坚决不去。小峰亲自登门赔礼道歉,要利用假期期间陪她去。她父母不愿见他,女孩最近情绪还好一点,为他说话,她父母才留他吃晚饭,饭后,他睡在客房。
他到她家去的那天夜里,月光出奇明亮。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到他房间来,他也没有睡,像一直在等她。她搂着他躺在明亮的月光里,要把自己给他。他看到了她的绝望与决绝,没敢要,觉得搂得像具尸体,甚至没敢吻一下。他给她唱赞美诗,她睡着了,泪水湿了枕头。
父母到底拗不过女儿,只好同意让小峰陪她去烟台。到了那儿,找到学校,发现是在郊区的一排厂房,有好多精神失常和忧郁自闭的孩子,还有好多老师和家长。老师多是基督徒兼职或全职,条件很简陋,但歌声笑声不断。一边祷告,一边学习,一边治疗,确实有很多孩子康复了。小峰请那位女校长安排她住在里边,他的奖学金差不多花完了,学费还没着落。他离开她回学校所在城市兼职,决定无论如何要挣够钱,帮她交学费,不花她父母的钱,好还上良心的债。她的好转看来很难了,他希望通过做了这一切之后,能比较心安地离开她,开始自己另外的生活。
就这样过了半年,她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她给他写信说:“我最大的病是不信主和不会爱,通过祷告和帮助别人,我的病彻底好了。”她成了一个基督徒。接到信后,千小峰兴奋地赶到烟台找她,发现她确实变了一个人,怎么说呢,虽说穿着朴素的衣服,但掩不住的圣洁美丽,焕发着上帝儿女的荣光,从来没这样美丽过。
他就劝她离开这里回去复学,冲动之下正式向她求婚。她不愿回去,决定留在这里帮助有需要的孩子,也拒绝了他的求婚,理由很简单:她不爱他。以前不过是被追求之下的某种虚荣心,才跟他谈恋爱的。爱不等于被爱。他努力用信仰的理由说服她,让她不要太狂热,她微微一笑,说:“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一个被主的爱如此改变的人,能不狂热吗?这又怎么能说是狂热?回过头来看,我怀疑你根本就还不是基督徒,你真的爱过我吗?”
他傻了。坐在回去的火车上,失望而又沮丧,信仰使他没敢得到她,又是信仰最终使他彻底失去了她。他忽然对信仰疑惑起来。如果信仰不能使一个人幸福而是使一个人痛苦,那何必信呢?他一下子没了信仰的理由。火车的晃动越发使他觉得像走在软泥上。
“也许,我确实不是基督徒,那我信的是什么呢?快乐主义?幸福主义?也许。上帝不过是用来到达快乐和幸福的桥梁。没想到的是,那位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上帝却利用我成了一道桥梁,让她信了这位还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上帝。”
窗外的庄稼地、树木和丘陵,飞驰而过,小峰仿佛第一次认真地在心底呐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上帝听到了他的祷告,就安排一个戴眼镜的基督徒刚好坐在他身边,问他有没有去过教堂。小峰一听就知道对方是基督徒,就假装说没去过。那个基督徒就给他讲了福音,讲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恰恰因为自愿受苦,为选民挣来了永生的福乐,从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恒久忍耐。关键不在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得到基督的爱,你在乎不在乎他的爱。
小峰听着听着,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跟这位主相遇过,也从来没有因着他的爱真正满足过。
直到此时,直到此刻。
那个戴眼镜的基督徒讲了半夜,小峰听了半夜,听到后来,头低下了。抬起来时,满脸都是泪水。
你也许早知道了,我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基督徒,坐在从烟台到南方的火车硬座上,下半夜时从小峰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写成了这篇小说,献给那个我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孩。
【作者简介】 本名:齐宏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72年生于沂蒙山区,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领域为基督教与中西文学。出版专著《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诗集《彼岸的跫音》,已在《文化中国》(加拿大)、《南京大学学报》、《中国比较文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基督教文化学刊》、《跨文化对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在《蔚蓝色》(美国)、《海外校园》(美国)、《钟山》、《青春》等刊物发表散文、诗歌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