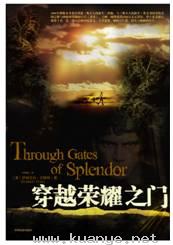旧约论启示的历史性和超史性
旧约是否应有一个核心,历来有争论,归纳起来不外乎为两种态度:有的认为应有核心,有的认为旧约无核心更合理。
Gerhard Hasel说:“圣经神学家既不能也不可拿一个观念,一个基要概念或公式当作系统,来排列旧约宣道信息的原则,或是当作从头决定如何展现旧约内容的关键。”不过他认为可以从旧约中“找一个足以把各式神学和纵贯的主题、观念和特色整合在一起的内在单—性,纵然那是一个隐藏的内在单一性”。“如果上帝是在启示他自己,那么就应该有某种关于启示的统一性,因为启示出来正是那同一位存在者”。既是启示是有机性的,并且神那有机性启示是体现在实际的历史之中的,我认为我们从“启示的历史性”与“启示的超史性”这两方面来认识可更好地把握旧约。
启示的历史性
首先有必要指出启示是指凡神参与的事,强调神的主动性。“最初只有神存在,只有神认识他自己。惟有他使一物受造,才会有另一个存在对他认识。”“启示之所以是必须……就是人因为罪而变成不正常……所以要改正人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的行动,必然是由神凭他的主权采取主动来成就的。”于是我们就会理解这么超越的神在人类历史中与人相遇了,以色列民的历史就是展现这样的一位神。希伯来圣经不难看出是镶嵌在整个历史骨架中。启示在历史的素材中被提示出来,“历史”正如瑟多布伦大主教所说的乃是“启示的工场”。是的,启示不是单指传递一套知识,而是指神在历史的自我彰显。神在自我启示中向以色列民运行了决定性、权威性、怜恤的作为,使以色列民在当中渐渐认识神是救赎主、创造主、赐福主。这种过程伴随着神一次次的再救赎和历史中的以色列民一次次再回应而进行着,神的启示与人的回应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甚至神的启示也屈从于历史的转变和偶然。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启示具有历史性且此启示不是命题式的启示(“命题式的启示”主张可以用命题的方式,客观地将有关神的真理作定义性、绝对性、超越时间的叙述)。正如骆振芳教授所言启示不是一些公式,乃是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在旧约中,神不是游离以色列民的历史外而启示,因此从神启示的历史性这一角度看旧约时,就会很平静看待关于旧约各个时段中神学命题为什么会有内在的张力与分歧。是的,毕竟旧约作为一个历史集成的记载,并不是从起先就给出一个中心主题然后作为向后展开的起点、轴心。就拿以色列民关于唯一神的崇拜为例,圣经中展现给我们的是以色列民时而专心敬拜耶和华,时而随从异教偶像的崇拜。这里问题的中心不在于神是否在开始就全盘启示唯一神的信仰,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确看见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神启示了自己。退一步说,即使神从一开始就全盘启示唯一神的信仰,那么他还是没有游离开历史而抽象进行。神在历史中“遵守”历史进程规律,“放手”让以色列民学效古代近东一些宗教崇拜。神在这之前并非没有自我启示,就神让以色列民多次经历其救赎、赐福和爱就足以让以色列民不应当忽略耶和华上帝,再者以色列百姓也常因学效偶像崇拜悖逆神而受管教,诸如此类的经历使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认识到自己得罪了那曾救赎及赐福与他们的神。就是在这样的张力中,磨擦中,以色列人渐渐在信仰上宣告唯一神的敬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理解今天的历史学者们所指责的“以色列的宗教并不是独创的,与近东的宗教是分不开的”。是的,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我们承认他们不是在真空中领受信仰,他们也实际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近东的风俗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这也好比“摩西的律法就与汉摩拉比法有些形式上的类似,约的形式也与古代的和平条约有相同之处,所罗门的殿和其它的古庙有雷同之处。”启示是在历史中进行,启示就有了历史的取向。虽然神对以色列民启示的某些形式可以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找到类似的形态,但是目的和意义大大不同。换言之,这一切历史中的事实不能成为神启示的拦阻,神的启示对他们仍然有其自己的意义。正如罗伯特·M·塞尔茨所说“因为以色列是一神教改变借鉴来的东西”。神的启示不是抽离历史,这是旧约一贯所表现的。不妨再从旧约以色列民被掳与归回这段历史时期来看神的启示。以色列民因悖逆神而被掳巴比伦,与繁华巴比伦一切诱人的事物比起来,“耶和华崇拜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利益呢?似乎神已丢弃我们,容忍我们被掳。敬拜神有意义吗”?生活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在脑海中常有这样的念头。而这时周边的民族“以东人、摩亚人和别的民族固然有他们自己的神,但这些神都认为是在他们的本国内被自己的人所崇拜的,无疑地,许多希伯来人都认定耶和华是他们民族的神,只应在巴勒斯坦的范围内受敬拜”。神固然借先知来晓谕他自己的心意,但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对此启示真正意义上的领受乃是到他们经历回归后。换言之,随着历史的进展,先知的话应验了,有了权威。当以色列民再一次经历了神果然对他们实行了拯救大能,耶和华神果然比一切异教之神都优越,就这样,他们在信仰上重申了摩西律法中所宣告的独一耶和华真神的崇拜。此外,被掳在他乡,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像耶路撒冷那样的圣殿崇拜,此时,他们的信仰似乎因历史的变更被“剥夺”了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们的信仰因着历史的变更却“更上一层楼”,“宗教显著地成为更属灵与更属个人的事,他们无法遵行那在圣殿中与崇拜有关的精细仪式,但他们的信仰倒决定地更有属灵的性质”。
可见,永生的上帝进入了人类历史,伴随着历史启示了自己的心意,人借各样的际遇在回应着神。人遇见永生神,因神在历史中自我给予、自我启示;以色列民宣告信仰,也可以说信仰告白无非是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和回忆;若启示是有目标的,则那个目标便是:在启示之神和回应之人类中间,建立相互的关系。旧约神学与以色列民族史的确是相携而行,神启示的这种历史性一直贯穿于旧约。
启示的超史性
旧约的确围绕以色列民族展开,但上帝作工的程序是从一个特别的存在到普遍的存在;即拣选一民族使他们的命运在诸民族中成为灯光和酵母,上帝的启示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也就是说,神的启示有历史性不等于说神的启示就陷入了特定性和时代性中,否则忽略了启示者是超历史的神。神的启示虽有历史性但也有永恒性,旧约对于昔日的以色列民以及如今的非以色列民和我们都具有意义与价值。圣经中神的启示是与全世界及其命运有关的。启示对于昔日有了永恒中的暂时性——历史性角度:启示对于今日就体现其本质的永恒性——超历史角度。
首先从罪的这一方面来看,创世记中讲到是神创造全人类,这也宣告了并非你我与旧约上帝无关。关于人的由来、万物的由来都应是古今中外人所需关注的,其中罪也是如此。“创世记的故事……透澈地洞察到人类生活的根本矛盾并具体地把它表现出来,那是人的本质和他在经验上的状态之间的矛盾,是作为上帝定意要他成为的人和他在实际上成为的人之间的矛盾。这里所叙述的既不是一处可以发现的地方,也不是一件可以决定其年代的事件,而是一项属于人类经验的事实……所谓犯罪并不是指在人类历史的过去中,某些可以决定其日期的原始灾难,而论到经常呈现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亚当”’。是的,不能认为罪只是一个关于亚当始祖的历史而已,应当从这个历史现象中看到每一个人。穿过历史的长廊,神的启示向今天的我们仍释放着永恒的信息,借着圣经上帝找到人并人找到了上帝的这种信仰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见证。说神启示信息具有永恒性,或许有些人就会问,‘若是如此,那么在旧约中神借摩西向以色列民颁布的律法、王国时期大卫王位的应许之约、神借先知所宣告的审判和讲说的拯救等等的记载应如何看待呢?对此我们要掌握三点:其一,我们否认应验先前启示的末后启示会改正或与先前的启示矛盾。其二,若是涉及到应许与实现的关系,我们不能否定应许有特定性与处境性,所以只能从整个历史事件完全的动态中看其意义。其三,也就是启示的超史性与新旧两约连贯性、整合性的问题。换言之,如何看待耶稣基督与旧约的关系。
我们说启示的超史性并不是否认基督是神启示的中心和高峰,相反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居住了,父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若“启示”就是神将自己给予人类,那么基督就是这种给予最集中的表现。不过将旧约各样的事物都看成是基督的预表、都指向基督,将是牵强附会的。基督所表明的是神启示不离开历史——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最直接的在历史中与人相遇;又说明了神启示中本质上永恒性——在基督里旧约的一切价值与意义被肯定了,无论是“约”、“律法”、“献祭”。也就是神在历世历代中愿意与人保持关系、视人为其伙伴的心意在基督里展露无遗。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旧约年代中为什么一些人竟会被称为义人和朋友,被神肯定。这除了基督比其救赎事件具有先存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启示具有永恒性的意义。
结 论
神启示具有的“历史性”并“超史性”以至使有限的人可以竟然与无限的神相遇了,同时旧约因着启示的“历史性”并“超史性”,旧约信息至少以神与人事件(双方的讲说和行为),以神救赎,人回应的走向等或类似的主线进行中体现出来。这样也就不至于失去把握旧约讲说神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就旧约经卷整体内容来说也是同样道理:旧约神学的形成应在三部分里即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而不能建基于某一部分以之为统筹全书的核心。
通过以上分析,在解释中既要掌握历史性、局部性,又要掌握超史性、整体性显得极其重要。在当今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中具备上述圣经观和掌握类似的释经艺术,将会产生积极的、合理的果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