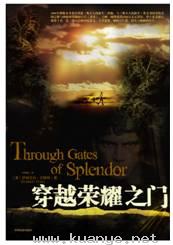失信仰所以失平安--评<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2004-12-18
作者:容光启
来源:来自网络我也要投稿
说实话,作为一个爱好文艺批评的人,我曾经对台湾的一些作家是有偏见的。譬如我以前对待张晓风的作品:觉得台湾这些作家怎么整天就谈“情”说“爱”的,什么“信心”、“爱心”呀,人性哪有那么简单?文学作品应该写人复杂的人性才是,揭示它,不管它是多么黑暗多么污秽,关键是“真实”,让人“震惊”,那才是好文学。现在,我知道,我这样的文学观,不是什么偏见,而是生命还没有到达信仰的境地。见到“真实”的人性之后呢?难道我们永远就满足于对人性真相的“震惊”吗?我们果真能不思“拯救”吗?
确实,“爱”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我们就是行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信”。我们首先“信”这个世界没有起源、没有终极、公义、仁慈和圣洁,一切只是“话语”, 是有背后的目的的。谁说“真理”谁就是“形而上学”倾向。我们首先确信这个世界没有无私的“爱”,“为人舍已”的“爱”,“爱邻人爱仇敌”的“爱”,然后才放纵自己的行为,在放纵中沉沦,在沉沦中虚无、怨恨。我们怀疑一切,唯独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不信”。
但是人的灵魂都是需要“安息”的,都渴望“自由”,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一个“不信”的人其灵魂可以得“安息”这是值得怀疑的,知识的增多不能增多生命中的平安和喜乐,理性不能给我们带来爱的能力和减少对死亡的恐惧,生命是否永远要处在恐惧、战栗的漂泊之中?我们真的情愿这样吗?
我愿意将台湾的张文亮先生的这本著作看作是教我如何求得生命的“安息”的书。张先生是美国加州大学水土空气资源系的博士,现在是台湾的生态学专家,真的是很感谢他,他的书让我对空气、水、土地里的动物植物有了一个亲密的认识。这本书极为有意思,故事的体裁应该是寓言,故事的对象是儿童,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与动植物有关的小故事让孩子们明白信仰的重要。张先生的故事都是以诗歌分行的形式写,而那些幽默的插图,将蜗牛、毛毛虫、蟑螂、小蝌蚪、河马一切可爱的不可爱的动物画得叫人忍俊不禁,倍感亲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小动物、小植物,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更没想到,这些上帝的造物,为我的生命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我特别看重《那一夜蟑螂教我怎么读书》这个故事(大意):
一天夜晚,我在读书时候睡着了,忽然似乎有人摇我,一看是只大蟑螂,蟑螂说要教我三招不武功。第一招叫“蟑螂爬墙功”,用手脚夹住墙壁爬上去。好怪的模样,难看的招式。蟑螂踢我一脚,我只好手脚并用,努力往上爬。爬上又掉下,蟑螂又踢我一脚,只好又再爬,愈爬愈会爬,愈知道如何施力才能舒服地往上爬。天啊!原来爬墙是这么舒服的事!忽然想到,读书不也是在寻找最佳施力点吗?
第二招叫“蟑螂冲锋术”,全身重心放低,弯下腰来向前冲!好帅的瞬间爆发力,就像百米选手的起跑姿势。我却跑不快,蟑螂踢我一脚,我才知,背后拖一堆漫画、电玩、电视,解下一些,还是跑不快,蟑螂又踢我一脚,只好再解下更多,果然愈跑愈快!啊!莫非自己把太多体力、眼力、智力,消耗在不当的地方?
第三招最难,是躺在地上的“蟑螂安息”躺在地上装死,太逊了吧!蟑螂又踢我一脚,好!好!我躺,安息还不简单?没想到满脑子的纷乱:色琴的、恐怖的、受伤的、愤怒的一大堆念头!我整夜反复挣扎,蟑螂这次没踢我,牠微微一笑,用踢我的脚指着天上:“啊!蟑螂能安息,是因有一位分担牠重担的主。”学习跟上帝一起担担子,是一生要学的最后一招!
这完全是一个卡夫卡的《变形记》的“信仰版本”。《变形记》写的是现代社会将人“异化”成一只外边是硬壳、内心软弱怯懦的“甲虫”(其实与蟑螂无异)。现代人这个“非人”的悲剧处境人们不去从“失信”的角度去解释,却仅仅解释为现代制度对人的“异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不同的是,卡夫卡笔下的蟑螂人“格里高尔”最终在恐惧中死去,而张文亮的蟑螂故事乃是叫人怎样得生命的“安息”。
在蟑螂教我的三招中,第一招属于一般哲理:读书求“智慧”也向爬墙壁,“寻找最佳施力点”;第二招属于特殊哲理:现代人为何如此愁苦,无法自由前行?其实是受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羁绊,“把太多体力、眼力、智力,消耗在不当的地方?”最叫我感动的是第三招:如何才能“安息”?
“安息”还不简单?我睡觉吧,我平静吧,我克制自己吧,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吧,——但是,果真能“安息”吗?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内心的“罪性”都在紧紧跟随,总是“满脑子的纷乱:色琴的、恐怖的、受伤的、愤怒的……”我的内心无法平息,恶念从生,就像伟大的使徒保罗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自由”吗?显然,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做什么,却不能!却做了!”因为人的灵里面还有一个与灵争战的“罪”的律,这个“罪”的问题不解决,人的灵魂不会有“自由”、有“安息”。
保罗的求告正是我内心的痛苦之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诚然,放纵自己是有快乐的,但那是“罪中之乐”,片刻的快乐之后是灵魂的不安和对死亡的恐惧。在这“取死的身体”中,怎能有“安息”!
显然,人如果自己能够找到“安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贫困的年代”,人就用不着像荷尔德林在诗中写道:
……像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迁徙,浪迹四方。”
(荷尔德林:《面包和酒》,孙周兴译)
必须要说明的是,“黑夜”并不神圣,神圣的是“光”。任何一个做“酒神”的“祭司”的人,结局是悲惨的。人们需要“神”,但总是奔错了方向。荷尔德林崇拜“希腊诸神”,意念是好的,可惜拜了别的偶像,结局是精神病;尼采沉醉“酒神精神”,以“超人”代替基督,最终也是发疯而死。他们都是在寻求“安息”,但却死得很惨。
如何才能得生命的平安?蟑螂指着天上:“啊!蟑螂能安息,是因有一位分担牠重担的主。”卡夫卡一生在绝望和虚无之中,“我的内心存在着可怕的不安。”(卡夫卡1913年5月3日的日记全文)卡夫卡的绝望成就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这样“杰出”的文学更加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的体认:“世界就是这般绝望和虚无”,这是一个可怕的“作者——读者”的循环。张文亮笔下的蟑螂与卡夫卡的“甲虫”的区别在于:“甲虫”体验的无法拯救(是没有看到拯救之途)让人死,而这里的“蟑螂”的启示则是:“牠能安息,是因有一位分担牠重担的主”;学习跟上帝一起担担子,是一生要学的最后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
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不能走太快,
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
次总是那么一点点?
我催他,我唬他,我责备他,
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
彷佛说:“人家已经尽力了嘛!”
我拉他,我扯他,甚至想踢他,
蜗牛受了伤,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啊!为什么?”
天上一片安静。
“唉!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
好吧!松手了!
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
让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
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
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快”着,“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岂不是逆世界的潮流?但是任何一个有“个性”人都知道,“世界”确实是一种“话语”,它的真相是永远隐藏的,追逐世界的人只是中了消费社会的消费机智而已,他自以为赶上了“世界”潮流,却是错过了与生命真相相遇的机会。所以保罗奉劝这样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人生“慢”下来是有必要的。
上帝为什么交给我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呢?在人的无边焦躁、怒气中,上帝的回答是一片寂静,而当人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把一切交给上帝,这时,奇迹出现了:蜗牛虽然缓慢地爬行,但是它带领我去的地方是为了领受一个巨大的恩典——一个花香四溢的花园!
上帝在教导我们学习人生重要的一个功课:“忍耐”,是为了让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忍耐”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忍”得一时的损失,是为了后面更大的利益;等等,乃是在“忍耐”中“爱”、“赦免”,无论邻人还是仇敌;乃是不管受怎么样的艰难困苦、患难逼 -/迫,都不与上帝之爱隔绝的“忍耐”。它与世俗利益无关。它的根基是“信”。只有“信”我们才有“爱”的能力。才有战胜一切权势的能力,包括死亡。所以,在这“爱”里,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的灵魂才真正有“安息”。
感谢张文亮先生的这本写给儿童的书,我的信仰之中的心正是“儿童”,它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滋养。张文亮先生将自己的信仰生活化成如此生动的故事、寓言和图画,通俗易懂,读起来让我们与信仰真道如此贴近,真是对我的一次赐福。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关键是我们的信心。
(作者为北京某高校中文系博士)
注:《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定价18元,选自台湾大学张文亮教授的《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昨夜我与一只橘子摔跤》,两书合成一本在中国大陆以《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为名出版,精美插图双色印刷。
说实话,作为一个爱好文艺批评的人,我曾经对台湾的一些作家是有偏见的。譬如我以前对待张晓风的作品:觉得台湾这些作家怎么整天就谈“情”说“爱”的,什么“信心”、“爱心”呀,人性哪有那么简单?文学作品应该写人复杂的人性才是,揭示它,不管它是多么黑暗多么污秽,关键是“真实”,让人“震惊”,那才是好文学。现在,我知道,我这样的文学观,不是什么偏见,而是生命还没有到达信仰的境地。见到“真实”的人性之后呢?难道我们永远就满足于对人性真相的“震惊”吗?我们果真能不思“拯救”吗?
确实,“爱”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我们就是行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信”。我们首先“信”这个世界没有起源、没有终极、公义、仁慈和圣洁,一切只是“话语”, 是有背后的目的的。谁说“真理”谁就是“形而上学”倾向。我们首先确信这个世界没有无私的“爱”,“为人舍已”的“爱”,“爱邻人爱仇敌”的“爱”,然后才放纵自己的行为,在放纵中沉沦,在沉沦中虚无、怨恨。我们怀疑一切,唯独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不信”。
但是人的灵魂都是需要“安息”的,都渴望“自由”,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一个“不信”的人其灵魂可以得“安息”这是值得怀疑的,知识的增多不能增多生命中的平安和喜乐,理性不能给我们带来爱的能力和减少对死亡的恐惧,生命是否永远要处在恐惧、战栗的漂泊之中?我们真的情愿这样吗?
我愿意将台湾的张文亮先生的这本著作看作是教我如何求得生命的“安息”的书。张先生是美国加州大学水土空气资源系的博士,现在是台湾的生态学专家,真的是很感谢他,他的书让我对空气、水、土地里的动物植物有了一个亲密的认识。这本书极为有意思,故事的体裁应该是寓言,故事的对象是儿童,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与动植物有关的小故事让孩子们明白信仰的重要。张先生的故事都是以诗歌分行的形式写,而那些幽默的插图,将蜗牛、毛毛虫、蟑螂、小蝌蚪、河马一切可爱的不可爱的动物画得叫人忍俊不禁,倍感亲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小动物、小植物,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更没想到,这些上帝的造物,为我的生命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我特别看重《那一夜蟑螂教我怎么读书》这个故事(大意):
一天夜晚,我在读书时候睡着了,忽然似乎有人摇我,一看是只大蟑螂,蟑螂说要教我三招不武功。第一招叫“蟑螂爬墙功”,用手脚夹住墙壁爬上去。好怪的模样,难看的招式。蟑螂踢我一脚,我只好手脚并用,努力往上爬。爬上又掉下,蟑螂又踢我一脚,只好又再爬,愈爬愈会爬,愈知道如何施力才能舒服地往上爬。天啊!原来爬墙是这么舒服的事!忽然想到,读书不也是在寻找最佳施力点吗?
第二招叫“蟑螂冲锋术”,全身重心放低,弯下腰来向前冲!好帅的瞬间爆发力,就像百米选手的起跑姿势。我却跑不快,蟑螂踢我一脚,我才知,背后拖一堆漫画、电玩、电视,解下一些,还是跑不快,蟑螂又踢我一脚,只好再解下更多,果然愈跑愈快!啊!莫非自己把太多体力、眼力、智力,消耗在不当的地方?
第三招最难,是躺在地上的“蟑螂安息”躺在地上装死,太逊了吧!蟑螂又踢我一脚,好!好!我躺,安息还不简单?没想到满脑子的纷乱:色琴的、恐怖的、受伤的、愤怒的一大堆念头!我整夜反复挣扎,蟑螂这次没踢我,牠微微一笑,用踢我的脚指着天上:“啊!蟑螂能安息,是因有一位分担牠重担的主。”学习跟上帝一起担担子,是一生要学的最后一招!
这完全是一个卡夫卡的《变形记》的“信仰版本”。《变形记》写的是现代社会将人“异化”成一只外边是硬壳、内心软弱怯懦的“甲虫”(其实与蟑螂无异)。现代人这个“非人”的悲剧处境人们不去从“失信”的角度去解释,却仅仅解释为现代制度对人的“异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不同的是,卡夫卡笔下的蟑螂人“格里高尔”最终在恐惧中死去,而张文亮的蟑螂故事乃是叫人怎样得生命的“安息”。
在蟑螂教我的三招中,第一招属于一般哲理:读书求“智慧”也向爬墙壁,“寻找最佳施力点”;第二招属于特殊哲理:现代人为何如此愁苦,无法自由前行?其实是受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羁绊,“把太多体力、眼力、智力,消耗在不当的地方?”最叫我感动的是第三招:如何才能“安息”?
“安息”还不简单?我睡觉吧,我平静吧,我克制自己吧,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吧,——但是,果真能“安息”吗?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内心的“罪性”都在紧紧跟随,总是“满脑子的纷乱:色琴的、恐怖的、受伤的、愤怒的……”我的内心无法平息,恶念从生,就像伟大的使徒保罗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自由”吗?显然,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做什么,却不能!却做了!”因为人的灵里面还有一个与灵争战的“罪”的律,这个“罪”的问题不解决,人的灵魂不会有“自由”、有“安息”。
保罗的求告正是我内心的痛苦之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诚然,放纵自己是有快乐的,但那是“罪中之乐”,片刻的快乐之后是灵魂的不安和对死亡的恐惧。在这“取死的身体”中,怎能有“安息”!
显然,人如果自己能够找到“安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贫困的年代”,人就用不着像荷尔德林在诗中写道:
……像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迁徙,浪迹四方。”
(荷尔德林:《面包和酒》,孙周兴译)
必须要说明的是,“黑夜”并不神圣,神圣的是“光”。任何一个做“酒神”的“祭司”的人,结局是悲惨的。人们需要“神”,但总是奔错了方向。荷尔德林崇拜“希腊诸神”,意念是好的,可惜拜了别的偶像,结局是精神病;尼采沉醉“酒神精神”,以“超人”代替基督,最终也是发疯而死。他们都是在寻求“安息”,但却死得很惨。
如何才能得生命的平安?蟑螂指着天上:“啊!蟑螂能安息,是因有一位分担牠重担的主。”卡夫卡一生在绝望和虚无之中,“我的内心存在着可怕的不安。”(卡夫卡1913年5月3日的日记全文)卡夫卡的绝望成就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这样“杰出”的文学更加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的体认:“世界就是这般绝望和虚无”,这是一个可怕的“作者——读者”的循环。张文亮笔下的蟑螂与卡夫卡的“甲虫”的区别在于:“甲虫”体验的无法拯救(是没有看到拯救之途)让人死,而这里的“蟑螂”的启示则是:“牠能安息,是因有一位分担牠重担的主”;学习跟上帝一起担担子,是一生要学的最后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
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不能走太快,
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
次总是那么一点点?
我催他,我唬他,我责备他,
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
彷佛说:“人家已经尽力了嘛!”
我拉他,我扯他,甚至想踢他,
蜗牛受了伤,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啊!为什么?”
天上一片安静。
“唉!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
好吧!松手了!
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
让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
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
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快”着,“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岂不是逆世界的潮流?但是任何一个有“个性”人都知道,“世界”确实是一种“话语”,它的真相是永远隐藏的,追逐世界的人只是中了消费社会的消费机智而已,他自以为赶上了“世界”潮流,却是错过了与生命真相相遇的机会。所以保罗奉劝这样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人生“慢”下来是有必要的。
上帝为什么交给我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呢?在人的无边焦躁、怒气中,上帝的回答是一片寂静,而当人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把一切交给上帝,这时,奇迹出现了:蜗牛虽然缓慢地爬行,但是它带领我去的地方是为了领受一个巨大的恩典——一个花香四溢的花园!
上帝在教导我们学习人生重要的一个功课:“忍耐”,是为了让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忍耐”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忍”得一时的损失,是为了后面更大的利益;等等,乃是在“忍耐”中“爱”、“赦免”,无论邻人还是仇敌;乃是不管受怎么样的艰难困苦、患难逼 -/迫,都不与上帝之爱隔绝的“忍耐”。它与世俗利益无关。它的根基是“信”。只有“信”我们才有“爱”的能力。才有战胜一切权势的能力,包括死亡。所以,在这“爱”里,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的灵魂才真正有“安息”。
感谢张文亮先生的这本写给儿童的书,我的信仰之中的心正是“儿童”,它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滋养。张文亮先生将自己的信仰生活化成如此生动的故事、寓言和图画,通俗易懂,读起来让我们与信仰真道如此贴近,真是对我的一次赐福。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关键是我们的信心。
(作者为北京某高校中文系博士)
注:《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定价18元,选自台湾大学张文亮教授的《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昨夜我与一只橘子摔跤》,两书合成一本在中国大陆以《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为名出版,精美插图双色印刷。
[ 赞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