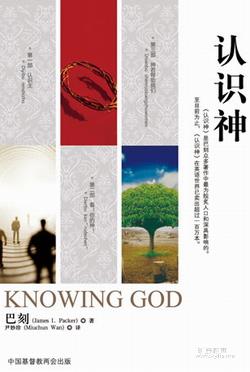罪是在上帝面前犯的——读《祁克果的人生哲学》
1。没有自我的人
祁克果(1813——1855,名字又翻译为克尔凯戈尔,基尔克果)是哲学家,又是基督教大思想家。谢秉德先生翻译的《祁克果的人生的哲学》一书,汇集了祁克果的六部论著。该书收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二部第二十三卷)”,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到如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收入这部书中的前三部论著是《今日的时代》,《我著作中的观点》和《致死的疾病》,我曾一读再读,爱不释手。我当然不信祁克果的话句句是真理,但他激励我思考,让我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的黑暗,这已足矣。祁克果屡次说过,他的整个写作事业“同时即是自我教育”,这应当成为我的座右铭。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的自我意识是蛮强的,周围的人也大都这么认为,但按照祁氏的思路,并非如此,实际上它并不发达,或者说很不发达。自我意识并非一个赤裸裸的自我而已,它与上帝意识直接相连,在天人,人我和物我的关系中反思自身。可是,多年来,我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知道天国在我心,更不明白灵魂中潜伏着恶魔,何论自我意识!
人是有灵性的,他心中有永恒的因素,这就是祁氏所谓的上帝意识。这也是他论述自我的根本之点。无论人是否承认它,都无法从心中除去它。无论人们用什么名字来表达它,都将以它为人生的基点,只是有真假之分而已。当然了,不信上帝的人也能事业成功,积赚金钱,家庭美满,诸事顺利,但是,“从灵性的意义说,这种人没有自我,没有一个为其值得冒险一切的自我,没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的自我;他们只是自私。” (注一)
一个人若不相信上帝,那么,他就无法知道我从哪里来,失去了根,或者说,他就必须承认我是从虚无中来,结果也是一样,他还是失去了根,因为虚无就是没有根。同时,他也不能知道我将向何处去,于是就绝了归宿,或者说,他要去的那个去处,本来无“处”,是绝对的空虚,完全的毁灭。在这两个虚无之间,他执意走自己的路,但那只是死路;他渴望成为他自己,但这个“己”或者“我”却是水中月、镜中花,表面上实实在在,但却无根无底,并且到头来却都化为空虚的空虚,从而完完全全地失去了那个本来就没有的虚幻的自我
在祁克果看来,自我是在上帝眼中的自我。因为人本来就在上帝的目光中,上帝一直注视着人,只是人闭着眼睛,不去面对上帝的目光。人的自我意识中包含了衡量自我的要素,或者是以父母来衡量自我,或者是以他人、国家和社会来衡量。衡量自我的标准越高,自我意识也就越高。但唯有以上帝为标准,自我才进入了永恒之中,而那本来就是他所在也应该在的地方。人的标准是神,而不是人,人“衡量自我的标准越高,自我意识也就越高;那么一旦以上帝为衡量的标准,自我的价值就无限地加重了。人越感觉上帝,就越有了自我;越有了自我,就越感觉上帝。只有当那自我觉得自己是于上帝面前之存在,只有那时这自我才是无限之我” (第147页),同一个道理,“人对基督的意识越多,他自己的自我也就越多,其本身在本质上也是什么。” (第180页)
这的确美妙!反过来,人若是以他人为标准,无论他怎么自视甚高,无论哥儿们怎么彼此吹捧,但 “他们对自己终不免看得太卑微,那就是说,他们不认知自己是灵性,是具有一种绝对价值;他们的自高不过在于与别人相比较” (第110页),而这一个比较,也不过是半斤对八两之比,比来必去,也比不出什么名堂,说白了,脱不了一个“俗”字。
2。我们这个时代
祁克果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来审视基督教信仰的。收入《祁克果的人生哲学》中的第一部书,就是《今日的时代》。
祁克果在《今日的时代》中严厉地批评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在本质上,乃是一个没有热情,只重理解和思想的时代,有时亦发出热忱,但转眼又如黠鼠般归于缄默。”(注一) 在这样一个不知价值为何物的时代中,“一切的事都只变成了念头而已”。(第6页)
把理解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是近代以来的时代潮流。笛卡尔鼓吹“我思故我在”,把“我在”和“我思”联系起来,“思”,或者说“理解”,就成了人“存在”的根据。培根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发展到了启蒙运动,就成了“理性就是力量”,“教育就是力量”,“社会制度就是力量”,这种种的力量,说到底,都是推崇“理解和思想”,而否认“信仰就是力量”。而信仰与思想一样,本身就是人生命中所蕴藏的力量。被剥夺了信仰之力量的人,他就只会从事理解,成了几条干巴巴的脑筋,信仰,勇气,热情,意志,就都被从人的生命中剥夺了。即使有什么勇敢与勇气,也被心智巧妙地转化为一种巧计。到头来,一切巧计都被运用去获得金钱,“人们所爱的唯一事物乃是金钱,而金钱变成人万事万物的抽象代替品。” (第7页)
这样的时代,全不知道行动或者决心的意义,大家都袖手旁观,夸夸其谈。人人都知道当走的路,而且知道各种不同的路线,只是无人愿意动身。因此,祁克果又说:“今日乃是颓坠” (第1页),从骨子里来看,就是心力的懈怠。于是,行动被宣传所代替,“我们的时代乃是一个广告宣传的时代,一发生什么事,就到处都是宣传。” (第3页)但从来不付诸于行动之中。
在这样一个空想的时代,“思想用尽各种所能有的方法,阻止世人了解他们与其时代都是同处于囚牢中——并非为暴君,权贵,祭司或秘密的警察所困,而是困囚于他自己的思想中;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困囚他,是因为它用一种自鸣得意的见解来欺骗人说,想象中的各种可能性,是远胜于一个决定的行动。” (第13页)其实,人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人的牢房,就因为这只是“我思”,而不是“上帝之思”,更不是在上帝之思引导下的生命之创造。
在这样“一个没有热情,只存在空想的世代里,妒忌便在消极方面成了一个联合原则” (第12页),于是就出现了祁克果所谓的“平夷运动”或者“平夷过程”,就像一个工程师平夷一块土地一样,把大家拉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平夷运动” 表现为把“平等”视为价值的最高目标,唯一目标。“平等” 成为上帝的代名词。“大家只注重‘平等’,总是说,有定数的人值得一个人为代表,人只要有那数目的人来拥护他,他的地位就算重要。。。近日则趋向一种数学式的平等,在这个平等的社会中,在各阶层都有差不多同数的人数来拥护某一个代表”。(第16页)
祁克果批评的是被近代人视为偶像的“平等”观念,并且,这种所谓的“平等”始于“被代表”直接相联系的,即一定数量的人由某一个人为代表。一般的人批评绝对的平等观,都是从人与人之间有不可抹煞的差别入手的,祁克果却是从灵性的角度着眼的,他始终着眼于上帝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人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抽象物。但“平夷运动”使一个人不再是属于“上帝,或自己,或他所爱的人,也不是属于他所献身的艺术或科学,他在凡事上,都只觉得他是属乎一个抽象物,受他心中的思想管制”,这个抽象物可以是代表他的集体,政党,组织,国家,也可以是某一个领袖,或者领导,人就这样地 “做了自己思想的奴隶”。(第17页)
就以实现人类平等的理想而论,按照世俗的平等观念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世俗之道本含着人间的种种差别,以不平等作为出发的条件”。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人的眼光来衡量是永远无法消除了的。只有从一种超越人的标准来评价人,人才可能有平等。这样的目光只能来自上帝。而上地看人的时候,是从高天上看的,他看到的是人心。因此,真正的唯一可能的平等,乃是“一种属神的,属本质的”平等(第46页),他是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且都实为上帝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堕落了,都是醉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要拯救的,都是上帝呼唤他归家的。这就是真平等,并且是唯一可能的平等。
但近代却高举起否定上帝的旗帜。平夷过程就是始于人拒绝认识自己是在上帝面前生存的。于是,就要扯平一切,把个人消失在“公众”或者“群众”之中,“因为群众既将个人变为一个组织中的分子,就使个人不负责任,忘却忏悔,或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 (第49页)
“平夷运动”为了把一切都降到一个平面,首先必须取得一种幻想作为其抽象精神,作为其代表。这个幻想就是“公众”。公众是“平夷运动的发号施令者” 。(第22页)多年前我学过的语录说的正是这样: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什么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但公众是什么呢? 祁克果尖锐地指出:“公众只是一个抽象名称”。(第23页)
“公众只是一个幻象。” (第23页)
多数人或者少数人都实有其人,都有其客观存在,但“公众”却没有其人,实际上也并不存在。 “公众是一个指万人的名称,但它无法被代表,或被检阅,因为它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虽然它在当代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名词。但它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是一种包含万有而终归于空虚无物的海市蜃楼”。(第22页)
与“公众”这个词直接联系的是“群众”这个概念。那么,“群众”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祁克果认为:“‘群众’只有数目字的意义,不论是权贵,富热,显达,凡事只讲数量,那就是‘群众’。”(第50页)
“群众”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怯懦”的代名词。从历史和现实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像群众那么怯懦的。当每一个人逃入群众中,而以群众为他逃避所的时候,他是因没有个人的勇气而避入怯懦中(他没有勇气去捉拿该犹,马流,甚至没有勇气承认他没有),他就把他的一份怯懦带给那号称‘群众’的怯懦群体。” (第50页)当一个人投入到群众中的时候,他就自己把自己抛弃了。于是人们在理始于现实中就常常看到,一旦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时,一个懦夫就成了英雄,胆小鬼就成了豪杰,而人民往往就成为“暴民”“乱民”的代名词。
群众是用投票来决定真理的,但真理却并不是依靠群众而以确立。无论是发现真理还是传扬真理,都要靠单独的个人,并且,真理也只对个人说话。“所谓真理,不外乎尊重每一个人,绝对地每一个人,而这就是敬畏上帝和爱‘邻人’之道。从道德和宗教的观点而论,接受群众为最后的裁判,乃是否定上帝,而亦正与爱邻人之道相反。” (第53页)
群众用数量作为道德的权威。凡是大家认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大家以为好的,就是最高的善。对此,祁克果提出了抗议,他说:就宗教信仰而论,无论男女老少,贵贱贤愚,“凡是感觉他在灵修上有了根基,而与上帝接近的人,都必然完全与我同意,作为‘集团’来做修养或被修养,是绝不可能的” (第60页)。道德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是这个人独自做出的选择和行动,并且也是这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辨别一个人是否配称为‘真理的见证’,须从道德上考验那人的言行是否一致,看看他的私生活是否代表他所说的话——不过这个条件,恐为如今这个只重体系,讲坛而不重人的品格的时代所摒弃。”(第64页)
“‘群众’乃是‘非真理’。” (第48页)这就是祁氏的结论。
我从自己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群众”是不存在的,“群众”是 0,存在的是代表群众的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他们是 1 或者 2。3。4,且排在 0 之前。若没有这些1啊2啊3啊,那个0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他们(1,像什么1号首长之类)才知道群众的利益、愿望和喜好,只有1号才能代表0号。什么“首长”啊,什么“首领”啊,什么“首脑”啊,这都与脖子以上的部分相联系,把“头”交给别人,由别人来做自己的头。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是说着玩的,是宣传!只有领袖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组织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天职是什么?听话而已。听代表自己的那个“群众”的话,这也就意味着自己无话可说,或者自己的话,根本就算不得人话,所以不说也罢。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当人把自己的话语权交给“群众”时,他就只是动物而不会说话了,虽然他获得了力量,但却失去了自我。所谓群众者,失去自我(个人)之谓也。
3。这个“单独个人”
“单独个人”,是祁克果思想的基石。在收入《祁克果的人生哲学》中的第二部书——《我著作中的观点》之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那单独的人。”祁克果曾有一个心愿,他死后如果有一块墓碑的话,那碑上只要刻上几个字就行了。这几个字就是:“那个单独者”,这也可以译成“那个个人”(第62页)。在这个群众被视为英雄的世代,做一个“单独个人”,它需要的不仅是大勇,还要有大智。在许多时候,人们嘴上说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坚持的却是“吾从众”,俗语谓之随大流。一个人若要成为一个“单独个人”,那他不仅要在认真思考之后对“生命”,“真理”和“道路”的有真确的见解,还要有选择走与众不同的路的勇气,他要敢于独往独来,特立独行。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单独个人”的,实际上,只有少数的人才称得上是“单独个人”。因此,人能不能通过“单独个人”这一雄关窄路,对于祁克果来说,就成了一个问题。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令人悲哀的就是,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他们的问题。
什么是“单独个人”呢?
“单独个人”,这“可能意味着唯一的个人,也可能意味着每一个的个人” (第58页)。祁克果如是说。
“单独的个人”这个范畴,不是社会学的范畴,而是灵性的范畴,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灵性上醒悟的范畴。就基督教而言,这个范畴“乃是决定性的范畴,它对基督教的将来也具有决定性。” (第65页)因为那“构成宗教信仰的基本条件,即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人。” (第60页)如此,才能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生命的主人是谁?或者谁对生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每一个单独的个人,一定不敢对在天的上帝提出诉讼,判定他与上帝之间,究竟谁拥有最后和完全的产业权。上帝必要成为决定因素。但是,作为决定因素的上帝,正与单独者相对称。若果‘人类’应是最后判决的法庭,或甚至只操有次要的司法权,那么,基督教就不啻是被取消了”。(第66页)群众并不拥有人生命的最高主权,只有上帝才有。
“上帝爱世人”,上帝对所有的人讲话,但听到的却是每一个个人。无论别人怎样说怎样行,我都必须对上帝有个反应,因为那是我的反应,是我必须独自做出的反应。别人,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组织、政党、民族、国家和全世界,都代替不了我的选择:我的灵魂必须独自面对上帝,或者“自己跳入上帝的怀抱中”(第39页);或者自己跳入到魔鬼的怀抱。
在宗教中,“个人是独自站在上帝面前。一旦在这一点上归于腐败,人就只好从团体中去找安慰,结果使人一生作了空想的奴隶” (第17页)。这也就是说:“信仰意味着个体性”。构成信仰的基本条件就是承认自己在全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渴望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独立地站在上帝面前,“担负他对上帝的本人的责任。”
无论人是否相信上帝在,但上帝一直在,且是我在的根基,且是一直在看着我,正像大卫所说得那样:“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注二)
基督教告诉世人,无论你是谁?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活着,“他若愿意,可以随时与上帝说话,而且一定会蒙上帝听到,总之,这个人是蒙上帝呼召,要他极亲密地与上帝往来!而且因为这个人的缘故,上帝降世,亲自诞生世上,受苦受难,这位上帝要求人接受他所赐的恩典,来作为他的帮助。” (第152页)
但这样白白的恩典却使人恼怒了,他既不能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又不能感恩地接受上帝的恩典。他的灵性死了,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强人。
祁克果强调,没有一个人能不成为罪人而认识上帝。只有当人感到了自己有罪,他才能进入基督徒生活之门。于是,“个人是在上帝面前生存的”,就变成了个人是作为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生存的。就像路德说的那样,人在上帝面前要成为一个实在的罪人,就是他的内心感觉自己有罪,他深深知道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在上帝面前是恶的。
4。绝望是致死的疾病
可普天之下,有几个人愿意成为一个实在的罪人哪?有,但不多。这个时代流行的口号是我就是上帝,这话口气大是大,就是不实。无论我怎么气盖山河,才华横溢,死到临头,万事皆休。
祁克果写了一本分量很重的书,名字叫《致死的疾病》。他认为,从基督徒的立场上来了解人生,甚至连死这件事都不是致死的疾病。但基督教却“发现了一个世人所不知道的灾祸,那就是致死的疾病”,这个“致死的疾病”是什么呢?它就是绝望。(第76页)
祁克果从自我入手开始分析绝望。他认为,人乃是灵性,灵性乃是自我,而“自我乃是那与自己的我发生关系的那个关系,或者说,自我就是那在关系中使这关系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人是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间的一个综合。总之,自我是一个综合。” (第79页)在这个综合中,自我既不要变为有限,也不要变成无限,而是“无限地脱离自我而向着无限,同时又无限地回到自我而向着有限。”于是,“一个自我是不断在生成的过程中,因为一个自我原不是自存的,它只是在那生成中。” (第97页)在这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自我意识是自我的决定性标准。” (第96页)
自我是关系,自我是在不断地生成的过程中,这是祁克果定义自我的两个基本点。
在两件事物(如有限与无限)发生关系时,那个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第三者,这种由两个关系(如暂时与永恒)彼此发生关系而来的新关系,就是人的自我。正是在这个关系中,才产生了绝望,有“两种真正的绝望:一是因不愿作他自己而绝望,二是因要做他自己而绝望。” (第80页)
为什么会这样呢?祁克果的分析是:人若要做他自己,就必须使自己与那产生整个关系的上帝(即权能)发生关系。他若想靠自己来做自己,就必然要否定那包含在他自身的他与上帝的关系,这就必然造成关系失调,“人的自我关系中的失调,也是使自我和那造成自我的权能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失调” (第80页),因此,通俗地说,绝望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失调。“绝望乃是人与自我在其应有的关系上的失调” (第82页)
绝望到底从何而来?在祁氏看来,绝望之产生,首先是由于人以自己为人生关系的中心。“绝望是由人生的综合以自己为关系之中心而来,更是因为那使人成为一种关系的上帝而来,让这种关系的发展,好像是脱离了上帝之手一般;那就是说,绝望之生,是源于人以自己为人生的关系的中心。” (第82页)
虽然人以自己为人生关系的中心,但人不能解除作为由无限与有限两者构成的自我,“人无法解除他心中的永恒成分,不,永远也无法解除它;人想要把永恒排除,那是绝不可能的;人每逢没有把持永恒,就是正在把它排除,但永恒却马上回来,这样,人就在每刻的绝望中招惹着绝望。” (第83页)换句话说,绝望就是拒绝以上帝为自己生命的中心。
近二,祁克果把绝望定义为“病至于死”。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死”,死本身乃是过渡到生命的一个过程,因此,在人的身体上并没有致死的病,死固然是病的最后阶段,但死却非生命的结束。说“病至于死”,“乃指死为最后之事。而这就是绝望”,换句话说,“绝望乃是病至于死。” (第84页)绝望的苦痛正在于它使人欲生不能,求死不得,求生无望。
如此这般,绝望就成为“一种最焦人的矛盾处境,是一种在自我中的深病,是永远不断地临于死境,然而却是死而不死,求死不得。”就像人濒临死亡一样,是“活着而体验死;这种经验若是一刻可能有的话,那即等于永远有。” (第84至85页)
人对于某事绝望,这只是绝望的开始,“真正的绝望,那就是对自己绝望” (第86页)因为人不能作他想作的,而他做出来的又不是他要做的,于是,他想取消他自己,但他又无法取消他自己,于是人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对自己绝望,绝望至欲消除他自己,这是一切绝望的定式。” (第87页)
“人绝望之不能毁灭自己,正是人绝望中的痛苦。人心中若未曾禀赋永恒,他就不会绝望,但绝望若能把他的自我消灭,那么,也就不会再有绝望” (第88页)。但这两点对于人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人就处在不断地绝望之中。
5.绝望症的种种形态
祁克果肯定绝望具有普遍性,即使人没有感觉到自己正在绝望中,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其性灵的深处,不是多多少少在绝望之中,并且,这个绝望并不是罕见的例外,这就是祁克果关于绝望的普遍性的概括。
同时,绝望也具有辩证的性质。但是,如果不了解人的灵性,就无法了解人的绝望。因为绝望“乃是一种灵性上的病患。” (第90页)从来没有在精神上感受到绝望的人,却可能正是绝望,“绝望所最喜欢停留之地,即是当前幸福的核心。” (第92页)“正如一切的心灵医生所承认,大多数的人通常是活着而不知道自己是属灵性的——就因为这样,他们乃觉得安全,满足,殊不知那正是害着绝望症了。反之,那些说他们自己是在绝望中的人,倒是那具有较深厚的天性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灵性的。(第93页)
古语说,哀莫大于心死。人生中最可悲的事情就是,许多人从来未曾深刻地认识上帝的存在,也未曾认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就是活生生地站在上帝面前存在。他们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平平常常地度过一生,但却不知道自己是属灵性的,虽然他们口中也知道什么认为万物之灵。他们心在绝望之中但思想对此却一无所知。而人对上帝的认识,“除非经过绝望,是达不到的。” (第94页)
在肯定绝望的普遍性的基础上,祁克果分析了绝望症的种种不同形态。
祁克果首先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分析绝望症的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无限”而生的绝望,它是由于缺乏“有限”而产生的。由“无限”而生的绝望就是幻想,“所谓幻想,乃是将一个人引领到无限之境,使他脱离他的自我,并阻止他回到他的自我。” (第98页)无论当人是在情感上陷入幻想,还是在知识上和意志上越来越虚张他的自我,使自己为幻想所驱使,但他都无法成为自我。
第二种形态的绝望是由“有限”而生的绝望,它是由于缺乏“无限”而产生的。“一个缺乏‘无限’的人是心意极端狭隘而精神卑鄙的”,他使自己完全有限化了,“他不再是一个自我,而只是一个人群中的数目,只是彼此相同的人群中的另一个单位” (第100页),让自己被别人夺走。从灵性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我阉割。
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安排要有一个他自己的“我”,独特的自我,有其独特之点,或者说特性,因此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独特之点“加以琢磨,而并非是将之磨成平面。他不应该因为害怕别人的议论,而不敢成为自己,更不应该因怕人而不敢表现其本质上所有的特性(人的特性正是不当削平的),其实,只有凭着人的特性,才有自我。” (第100页)
但是,不敢成为自己的这种类型的绝望之人,却像祁克果所形容的那样:“他圆滑像一个水中磨过的石头,光滑就像一块在人手中转来转去的银钱”,(第101页)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如何地患着绝望症,他在世上仍能完满地过生活,甚至因此而顺顺利利;他于追求今世之一切生命目标时,倒常受人赞许,尊崇,敬仰。因为所谓世俗,正是有这种典型特质本身以适应世俗而成的。” (第102页)
祁克果从可能与必然的关系又分析了绝望症的两种类型。
一个开始存在的自我,它既是属于必然性,同时也属于可能性,“就其已有的自我而言,它乃是必然的;就其所需生成为自我而言,它乃是可能的。” (第103页)由此就产生了两种类型的绝望,由可能性而生的绝望和由必然性而生的绝望。
由可能性而生的绝望是由于缺乏了必然性:它使自我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各种可能中挣扎,但却“不能脱离那地点而行动,也不能达到任何地点。因为‘必然’正是据点;要成为自我,正是要在某地点行动。” (第103页)拒绝行动,就不可能使任何一个微小的可能成为现实,于是,自我就没有现实性。
造成这种绝望的原因是因为人缺乏 “顺服的能力,即顺从人本身的必然,这内在的必然性亦可以称为人自己的限界”,此种人不知道他的那个自我“乃是一种固定有限的,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反之,他因只顾到可能的,幻想的自我,就丧失了真的自我。” (第104页)
与之相反的由必然性而生的绝望是由于缺乏了可能性:人若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可能的关头,他必然陷入绝望之中。这样的人,祁克果称之为“定命论者”(“宿命论者”)和琐屑论者。对于“定命论者”来说,一切都是必然的,必然律就是他们的上帝;对于琐屑论者来说,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就是他们的上帝。二者都封闭了任何可能。
祁克果特别从信仰的角度分析了可能性,他说:“最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上帝凡事皆能。这事是永远地真实,所以也是在每时每刻上皆真。”但人只有到了山穷水尽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时候,“才能决定地肯定这真理。那时候,问题乃是,他是否真‘信’在上帝凡是皆能。但是,这正是他放弃了自己的理解力的道路;信乃是人为要得着上帝而放弃自己的理解力。” (第105页)
人生的奋斗,就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断地争取可能,为“可能”而竭力奋斗。在这一场争战之中人成败与否,“全凭他是否定志要为自己争取可能,那就是说,他是否有信心。” (第106页)他知道,从人的方面来说,他是必然要灭亡的,但他仍然相信有可能靠上帝而得救。他知道,在上帝凡事皆能,时时刻刻都能,这就是解决可能与必然之矛盾的健全的信仰。
由此祁克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祈祷乃是呼吸,可能之于自我,如同氧气之对呼吸一般。”因为“为要使祈祷有可能,就必须有一位上帝,那就是说在自我之外还必须再加上可能,因为可能是创造的原则。上帝就是那凡事皆能的存在,而凡事皆能的原则即是上帝。只有那在心灵深处受着感动,以致了解凡事皆能而因此使自己成为灵性的人,才能与上帝接触往来。正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属于可能,才使我能向他祈祷;倘若上帝的旨意只是属于必然,则人就只好哑口无言了。” (第108页)
祁克果从意识方面去分析绝望,又概括出了绝望的两种类型:没有被意识到的绝望和人感觉到的绝望。绝望与人的意识有关,意识越是加深,绝望也就越是加深。没有被意识到的绝望,就是不感觉到自我甚至永恒而生的绝望。这种人过惯了情欲的生活,他没有勇气来过灵性的生活(第110页)。
这种人经常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什么也不害怕。“那不感到在绝望中的人,是更不觉得他自己是灵。而不感觉自己是灵,那正是绝望,是丧失了灵性。” (第112页)这种没有感觉到的绝望,是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绝望。“因为绝望症的特征,乃是不觉得自己是在绝望之中。” (第113页)因此,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灵性的,从而皈依上帝的,那么,无论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无论他如何地享受人生,他的生存终究都是绝望。
与上面这种类型的绝望相对称的,是感觉到自己患了绝望症而来的绝望,这种绝望的产生,或是由于不愿意达成自我,或是由于想达成自我。
人由于不愿意达成自我而产生的绝望,是由于心志软弱所生的绝望。它首先表现为对世俗之事的绝望,外在的事物使人挫折,站立不住,于是,他陷入绝望之中。以后,一旦有外来的援助到来,他就又重新生活。他没有自我,即使在绝望中也没有达到自我。他对事物只是采取直接反映。另外一些人,虽然他们也能够做自我反省,但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还无法认识到自我之中包含永恒。
对尘世的绝望其实是对永恒或者对自我的绝望。因为它将世上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因此,这就是对永恒的绝望。这种绝望是由于人感觉到了自己的软弱而产生的绝望。“他在绝望中不能忘记他的软弱,所以恨自己,不肯在他的软弱上凭信心使自己谦卑,以便再得着自己。” (第130页)一般说来,这种类型的绝望是稀少的。
祁克果分析了另一类的想作自我的绝望,他称为灰心失望地愿做自己而陷入绝望违抗行为。在这里,人不愿意丧失自己来重新生活,他想摆脱自己已创造他自己,使自己在无限的自我的帮助下成为他所愿意成为的自我,“在每一件事上,他能够武断地重新做过。不问他把一个思想推演到多远,一切仍在假设之中,这样,自我不但不能越来越成为他自己,反而越来越来表明,他不过是一个假设的我。”虽然这个自我是他自己的主人,但却可以断定,“那作主宰的没有可以统治的国家,他所统治的是空的;他的国度和地位是受辨证律之支配,随时都可以起g e命的。最后他所靠的,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于是他就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海市蜃楼,直到自己也沉没于其中。(第135至137页)
无论人如何要成就自己,让自己成为一切,但他绝对成为一切,于是只好绝望。
人以史为镜,以人为镜,镜镜都照出了人的不完美。柏杨写了本书名叫〈丑陋的中国人〉,有评书人说丑陋的柏杨,都是妙语。但更妙的是圣经上说的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若人看到了自己如此陋和污秽,他怎么愿作他自己呢?可他不愿又能怎么样呢?他就是那个样子,砸不烂,除不掉,也摆脱不了。人之所以绝望的,正是他无法自己取消他自己。人要统治一切,但他的统治是空的;他要得到平安,但却为焦虑所笼罩;指望靠越来越多的东西满足自己对幸福的渴望,结果是什么?火上浇油,或者说,水中捞月。
6。绝望是罪
罪是什么?罪是绝望。祁克果认为这里的要点是在于“在上帝面前”和“有了上帝观念”这两个概念,因为“那使人的绝望成为罪的,就是因为涉及上帝观。” 人的过错之所以成为罪,正是因为是在上帝面前。(第143页)
自我的要素之一,就是衡量自我的标准,使基督徒与异教徒相区别的,就是衡量自我的标准,是以上帝为标准?还是只凭人性的我作为标准?
于此,祁克果定义说:“罪乃是:人在上帝之前不愿做他自己而陷入绝望,或是人在上帝之前要做他自己而陷入绝望。” (第147页)这样说来,罪的反面就不是什么德行,而是信心,“罪的反面为德行,那是一种异教徒的看法,因为他们只以人的标准为满足,而不知‘罪’的特征乃是在于罪是在上帝面前犯的。罪的反面不是德行,而是信心:正如罗马人书(14:23)所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整个基督教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定义:罪的反面不是德行,而是信心。” (第149页)
什么是信心? “信心乃是:自我之作自我,或定意要作自我,须明明白白地靠上帝。” (第149页)这可以看成是祁克果的定义。
“在基督教的每一个教义中必须要着重它是含有冲撞人之可能性,”从而防止信徒想入非非,就罪的定义而论,它所包含的激怒人的因素就在于,“它肯定个人是直接站在上帝面前,因此他的罪是为上帝所关心的。” (第149页)这个关心既包含上帝恨恶罪,不愿意看到人由于犯罪而走向死亡;又包含上帝要拯救罪人,使人不再在罪中沉沦,从而获得永生。
这对人来说实在是太奥秘了,完全无法理解,他如果不接受,就必定要否认它。
苏格拉底定义罪是无知。一个人做错事,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事是对的。祁氏说,不对。这个苏格拉底的定义缺少了意志,就是违抗上帝命令的意志。基督教证明,“罪是源于人的意志,而不是由于人的心智;人的意志之腐败是远过于他所意识到的。” (第162页),由意志的概念,基督教达到了违抗行为的概念。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思想却勇气不足,它“不敢承认人能明知故犯,不敢承认人知道什么是义但却去行不义”。(第161页)
在祁氏看来,“人不能靠自己并且由自己来解说何为罪,因为人自己是陷在罪中。他所有关于罪的谈论,骨子是要替罪说话,想凭原宥推诿,以减轻自己的罪。因之,基督教乃从另一个途径开始,宣布人必须从上帝那得着启示的训诲,才知道罪是什么。罪不是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义,乃是因为人不愿意知道它,更是因为人不愿意去实行它。” (第16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可以说罪乃是无知,即“人不知何谓罪。” (第162页)
由此,祁克果区分了“不能了解”与“不愿了解”的区别,“人之所不知是因为他不愿知,而人之不愿知,是因为人不肯志于义。。。人即令懂得何为义,也是要做错事的,或说,人明知何为义而不肯去行义。” (第161页)
据此,祁克果提出:“你如何信,就如何行;或说,你如何信,就如何为人;人如何信就如何在。” (第160页)
在以上的基础上,祁克果进一步定义说:“罪乃是:人凭上帝启示知道何为罪之后,于是在上帝面前不愿意做他自己而陷入绝望,或是在上帝面前定意要做他自己,而感到绝望。” (第162页)
祁克果严厉地拒绝那种认为人能够凭借理解来了解基督教的思想。他认为,理解基督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整个基督教都以凭信心而不凭理解为关键,”人如果不信,就不免感到恼怒。一切理解的企图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对那本来不愿意被人理解的事却要用理解去理解它,这岂不是愚笨鲁莽。“人相信或不相信,只是信心的问题。” (第163至164页)
基督教坚持,“必须从上帝得着启示,然后堕落了的人性才知道何为罪,而且坚持这启示既是信条就必须为人所信。”(第163页)因此,不能认为罪只是消极的,只是软弱,无知,情欲和有限,那是泛神论的思想,是理性主义。在基督教看来,罪不是消极的事,乃是积极的。罪“之所以是积极的,乃因它是站在上帝面前。” (第166页)
7。罪的连续性
祁克果说:“人之陷入罪中的每一刻是一种新罪,或说得更精确些,他之陷入罪的境地即是新罪。”因为“永恒的本质乃是在于连续不断的意识”,或者说,永恒要求人要不断地意识到自己为灵性,并且有信心。“永恒只承认两种境地,若不是属乎信心地即是罪;凡未曾悔改的罪即是新罪。” (第171页)因为人如果不脱离罪,罪就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人之留在罪中,较之所犯的每一个别之罪更坏,“他之留在罪中便是罪的连续,每刻是一个新罪。”因为罪的本身是一贯的,罪的本身中具有邪恶的一贯性。(第172至173页)
“基督教的道理是从世人的罪开始的。罪的畴是属个人的。光凭玄想,人绝想不到罪究竟是什么。” 并且,人想到罪不能不想到罪人,就如人想到人不能不想到个人一样。对罪“唯一认真的看法,乃是认你与我都是罪人。”(第185页)正视罪乃是认识它在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不问这个人为你为我,但你我却因认罪而得认识自己,并且叫自己以罪人的地位对罪牢牢负责。
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表明,人与上帝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更准确地说:“上帝和世人之间,在品质上具有无限的差异。” (第193页)“人与上帝之不同,根本上因为人是一个罪人,再没有什么差别和这相比的了。” (第188页)罪是人的品质中唯一不能归与上帝的事物。
因此,人唯一的路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上帝是上帝,而我是一个罪人。老老实实地认罪悔改,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罪人。
定稿于2004年4月
注释:注一,祁克果 著,谢秉德 译,《祁克果的人生哲学》,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86年3版,第102页。(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二十二卷),以下引该书只注明在本书中的页码。
注二,《圣经》(和合本),《诗篇》第139篇第2至3节。
【作者简介】 范学德,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19岁入党,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1985年考入**中央党校,获硕士学位。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哲学多年后,于1991年秋来到美国。在教会中与基督徒激烈辩论信仰三年半后,于1995年年初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一年后到慕迪圣经学院读研究院。毕业后他经常在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布道,其它时间从事写作,出版了《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心的呼唤》、《梦中山河——红小兵忏悔录》、《活在美国》和《细节中的文明——寻找美国的灵魂》等十多本书。